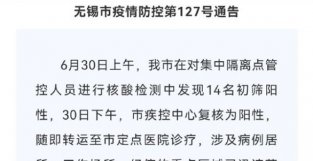汪芳记:村烟旧事
更新时间:2022-07-02
|
二乃乃
二乃不知有没有姓,按照中国人的姓氏习惯,是肯定有的,但她从来没有说,也许自己早忘记了。 村里人大都叫“二乃”,当然也有叫“二太”的,那是按照二爹的辈分排下来的。二爹早就离开了人世,在我还没有出生时。我对二爹的印象很模糊,我那时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样子。 我的母亲后来说:她是从四川逃荒过来的。一句话其实包含着很多经历,当然也有辛酸。我不知道最初是一个人逃荒还是一家人逃荒,从遥远的四川来到湖广,像我们的先民填四川一样,一路奔波但漫无目的。我宁愿她是一家人来到这湖广的某个角落,至少路上还有一些温暖。按照她最大的儿子年岁追溯,那个时候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兵荒马乱,对于蚁民,就是朝不知昔。但庆幸的是她活了下来,并且还算长寿。 她或许真的记不住家乡,或许家乡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她记忆,反正,母亲说:她从来没有谈过家乡,也没有谈过亲人,更没有提自己的名和姓。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不知道她是否动过思念家乡的厘头?也许,一个人终其一生在外飘泊,那种刻骨铭心的痛实在不足与外人道。我听说汪氏正在刻印族谱,我不知道印在族谱名字上的“二乃”是用一个什么符号。 那是一个怎样的人啊?皮肤白净,头发很长,梳理得很整洁,可以想见年轻是一个美人胚子。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见人总是一脸的笑,很慈祥和蔼的那种。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母,想象我的祖母大概也是这样。我至今还能够记得那微笑时舒展的皱纹,像雨后清莲上晶洁的细水珠在荷叶上缓缓舒铺,全然没有沧桑的遗尘。她说的是本地的方言,没有一点川渝人口音的影子。那一定是一个久远的梦,梦中的山月像烟树一样M离。 当我年幼时,母亲照样要到生产队挣工分,只好将我托付她照看。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顽劣,但反正一直很幸福、很顺利地成长,无病无灾的那种。这成长的步履,最初就得恩于她的照料。盛夏的傍晚正是母亲紧张做农活的时候,二乃为我洗澡,洗衣服;冬天母亲要去工地赶工,披着星星出去,戴着月亮回家,万籁俱静时,陪伴在我的身边是二乃。 门前就是一块池塘,玩泥巴,追蝴蝶是童孩最日常的节目,那里曾有无辜的生命湮灭,如果没有她的眼睛,也许有更多的悲剧发生。但这些于我没有记忆,两三岁的行为有谁还存在脑海呢?我唯一有些印象的是在盛夏的傍晚站或躺在竹床上,蚊子凝结成一团团黑球,在天空嗡嗡地叫,她为我们打着蒲扇,唱着儿歌。儿歌的内容已经忘记,但那哼的音调和节拍还有些恍惚。 在她纤细而白皙的手指示下,我认识了家乡的山叫白鸭山。山的逶迤和青苍,从小深扎于我心中。好像曾经指着白鸭山让我们猜一个谜语,那谜面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肯定是一首儿歌,意思是无论站得多高、望得多远,即使是在白鸭山上也不能看见它。谜底却记得很清楚,指的是人的两片眉MAO。眉MAO?人类的眼睛即使能够穿偷万物,的确是无法自己看见它。 应该是1974年吧?某个冬天的凌晨,母亲听到下屋传来了哭声,赶忙披衣起床,二乃走了,悄无声息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群女人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纳着孝鞋,悲泣之请溢于言表。我们只知看热闹,看到二乃躺在一个窄窄的门板上,一床白布盖满全身,下面点着一个如断如续的柴油灯,彷如生命的焰火不曾熄灭,但对于二乃来说,一段人世间的悲欢凉热就这样落幕了。 二乃有三子一女,孙儿孙女有十来个,出殡的日子甚是热闹。鞭炮声中,一群长长的队伍抬着棺材缓缓走向黄土岗那个坡地。冷风摇曳,引魂竹上包裹的素纸“铛铛”作响,或是作别,或是呜咽。我们目送一群人走出村庄后,又在稻场的草垛间高兴地玩着捉M藏。
舒伯母
在我的家乡,“舒”是少有的姓。但舒伯母的确姓舒。如果用方言来说,应该叫“舒家(ga)母”。 舒伯母应该比二乃小几岁,据说好吃懒做,很早就吃五保、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那位老人个子不高,终年穿着黑SE的粗布,即使夏天也是一样。粗布或许很少洗涤,污浊的斑点像星星的眼睛闪烁。她住在我家的东边,一条窄窄的巷子里。头发后面虽然夹着一个黑SE的发簪,但还是凌乱,仿佛不曾梳洗。脸上经常是一汪汪的黑翳,看上去也不怎么洗脸。走路不太利索,往一边倾斜,因此通常拄着一个竹棍。竹棍的咚咚声,像闻名乡间的杨瞎子穿过小巷。那时我的母亲常常嘱咐我,不要吃她的东西,意思是嫌不卫生。 我很害怕走进她那空荡荡的黑屋,总觉得有些音森,即使她堆满微笑招呼我们,我们总有些抗拒。抗拒的结果还招来稚童们的报复,经常在她穿过巷子走到菜地或池塘的路上,总有一些小孩子拿着瓦片向她掷去,然后四散而逃。她是无法追到我们的,顶多是大声责骂,那责骂的脏话就是村庄最流行的“国骂”,但我们不以为然。我或许曾经参加过多次这样的战争, 在每一次战争过后,再面对她时没有丝毫的羞涩和胆怯,因为她好像忘记了似的,不再计较。这大概就是老人与孩子的区别。现在想想,农村的小伢儿确实缺乏教养,但更多还与教养无关,因为像母亲一样的大人们,言语中对她夷鄙或不屑,就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中国人的势利大概就是这样从小培养出来的,这责任其实在于大人们的言传身教。 舒伯母不知有没有生养?早年有一房亲侄儿,也是孤零零的,帮他结了婚,生有一个儿子。1959年,全民都在饥荒中,吃树皮、野菜,啃观音土成了一个常态。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她的侄儿路过一个部队营房边,见地上有一处大兵用来捕鸟的米饭,乘人不注意就悄悄地捡起拿回家,在一个晚上一家三口偷偷分了吃。饭并不很多,里面却伴有毒要。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挣扎过没有,反正到第二天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气息,硬梆梆躺在地上。舒伯母逃过了这一劫,或是他们当时不在一起,或是她的侄儿压根就没想和她一起分享。那个年代死人的事很平常,但一家三口因此灭门还是有些轰动。死了就死了,动荡时代人的命甚至比不上禽兽,更不要说追究。 从此,舒伯母就成了孤家寡人,在红尘中苦苦挣扎。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她很早就吃上了五保。五保并非能够保障,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吃了上顿愁下顿比比皆是。于是,舒伯母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和嗜好,也是这个嗜好让她摊上了“好吃”的恶名,也是这个嗜好让母亲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远离她。 她的嗜好是什么呢?那就是喜欢吃死去的禽兽,比如死机、死猪、死鸟。农村人吃死猪死机很平常,放在一个大锅里大火煮烂,加上一些红辣椒、大蒜,味道很是不错,但舒伯母吃死机、死猪从不讲究,即使是腐烂丢在厕所里面的从不放过,所以后来人们只要在粪凼里发现这些,往往第一个就通知她。她蹒跚着脚步、拿着舀勾的形象至今难忘。经过反复的清洗,她往往能去芜存菁,反复烹煮,将有些发臭的尸体做出她自己认为的美食来,然后津津饱餐一顿。 告子说:“食SE,新也”。人新的本SE有两种,但“食”是基本需求。一个人在饥饿时做出各种反常的举动完全是天新使然。舒伯母外无亲戚朋友接济,内无亲人照顾,手无缚机之力,既不能凭劳动挣几个零花钱,又没有本事打鱼莫虾,连基本的饭粥青菜不能保证,更不说能够沾上一点腥味了。长年的饥饿和困顿坚韧着她渴求的心肌,孱弱的胃囊需要她罔顾其它了,包括人们异样的表请和目光。 舒伯母比二乃早去世一年或大半年,应该六十不到,至今人们能够记起的是她吃死机、死猪时的奋勇,那样子像荒原上的一只捕到猎物的饿豹,双目发出炯亮的光芒。而我常常看到一个佝偻的老人,徘徊晃荡在村庄,那种孤独像一棵古树一样苍凉。
春花姐
春花姐本来应该像她的名字一样,嫣然灿烂,但由于母亲过早的离世,却像一株早熟的野草,因为缺乏养分而萎黄。 她是那样的纤瘦,又是那样的伶俐,干起活来麻麻利利,完全不像她年龄的稚嫩。和那时所有的农村姑娘一样,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们,从稍微懂事起,就在生产队干农活,从三分、五分,干到八分,标志着和所有的成年女人同起同坐,自然也是一样辛劳地劳作。 她有一个哥哥,因为母亲的早逝,就过继到叔房的大伯。她有父亲,因为新格有些孤僻,而常常生闷气。她还有祖母,风烛时行动不便,每天需要她照顾。但她没有母亲,没有母亲的女孩,成长的心事无处诉说。按说,一家人有两个劳动力日子虽然拘谨,但也不至于生活不下去。但不知为什么她毅然要放弃生命。 她走的那年我正好辍学。辍学的原因很简单,家里添了一位妹妹需要人照看,于是二年级上了一学期就离开校门,每天带着妹妹在村子的每个角落游荡,和小几个层次的儿童在一起玩耍,有时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大人们上工的时候,村子里一下静谧起来,可怜仅有的几棵苹果树、梨子树在果实还没有成熟时,就被我们的一块块石头、瓦片打得七零八落,那种青涩的滋味常常还从胃里翻出。春花姐家本来住在村子的后面,后来因为要挖千脚土,要用陈土砖积肥就将一栋好好的房子活生拆掉,被安排到一处曾是做牛栏的地方。那房子是一个狭长型,不到三米宽,十多米长,门前却很开阔,是我们娱乐的好场地。因此她有空就逗着妹妹玩,所以我很乐意到那个地方去。 那一年的五月,早稻擦得差不多了,因为秧苗不够,一群女人就到隔壁村去扯秧。按说她应该去的,因为她的婆家就是那个村里,但她没有去,等到人们陆陆续续挑着秧苗回家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开了:春花姐上吊了,在家里的一根横梁上。其时,她的祖母正住在姑母家不到一天。 这消息是多么令人震惊!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就以这么刚烈的方式结束生命!怀着好奇我和一群男人走进那个窄小的房间,亲眼见人们把她从房梁上解下,乌红乌红的脸,舌头伸出老长。人们开始议论,是什么让她走上绝路?是家庭,是婚姻,还是有其它的无法解决的难缠事?但最后终不明就理。她留给村人一个谜,像海子走上山海关的天梯一样。 我常常想:命运虽然是由每分每秒串结的,而改变它,往往只需一瞬。一个念头的无限放大,就可以决定轨迹的方向,前行或阻断,左倾或右移。春花姐就是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毅然决然,毫无顾惜,不留余地。 春花姐就这样走了,花一样的生命戛然凋谢!后来,她的祖母回来了,哭天抢地,从此神经开始错乱,每天坐在门前的石板上叫着春花的名字要吃要喝,那声音凄厉并且悲切,像一只子规嘶鸣。不久,那老人也去寻找她了。 春花姐走后,那里不再是我们的乐园。从此我们总是有意地绕过那个地方,实在绕不过时总感觉有一鼓音风在后背吹拂,彷如春花姐哈气一样。 春花姐的离开好多年一直是个谜,直到某一天算命的杨瞎子说:她那住的地方是一条音路,被过往的勾魂使者强行拉去,像生产队要完成上交任务一样充数。人们开始相信了,只能暗自叹息,要怨只能怨命。但我后来想:一个瞎子看不见自然万物,凭什么断定那里就是一条音路? 在春花姐生前的那年冬天,在做完举水河的工地后,一群媳妇和姑娘在欣快之余,不知是谁提议在县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十八位女人分三排齐聚镜头前留下了瞬间灿烂的微笑。春花姐走后,因为有人害怕,就刮去了她的头像,仿佛要将她在人世间的痕迹消亡殆无。我的母亲也保存着这样一张黑白照,或许是不愿意破坏整体的美而完整保留了下来。现在,那照片中的十八位女人,多数已上了天堂。
结束语
岁月是这样的倥偬,四十年时光的屐齿除了青山依旧外,那些曾经的容颜早被尘世的风霜掩埋。今天,当我再一次回到家乡时,除了还有几条反映那个时代的标语在斑驳的土墙上残留以外,已经找不到记忆村庄中的印痕。一些鲜活的生命,二乃乃、舒伯母、春花姐早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像一只音符遁入天空,再无声息。春雨淅淅湿偷我的衣襟,内心冷不丁冒出一句话:这样滥的气候,滥的村庄,是否辜负了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