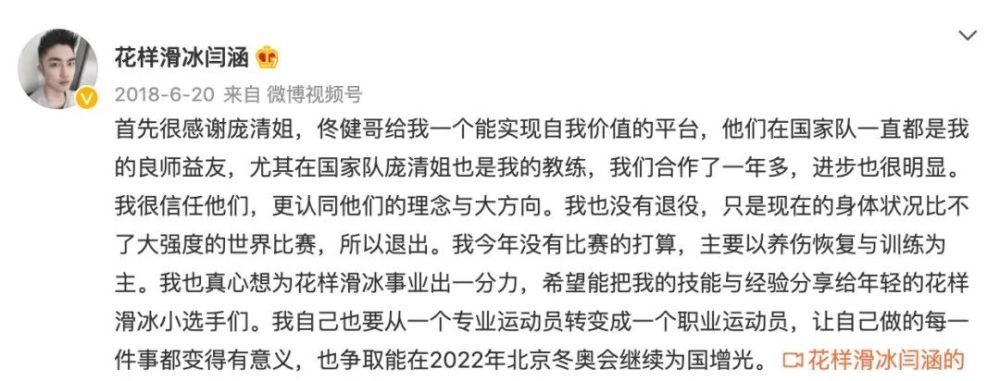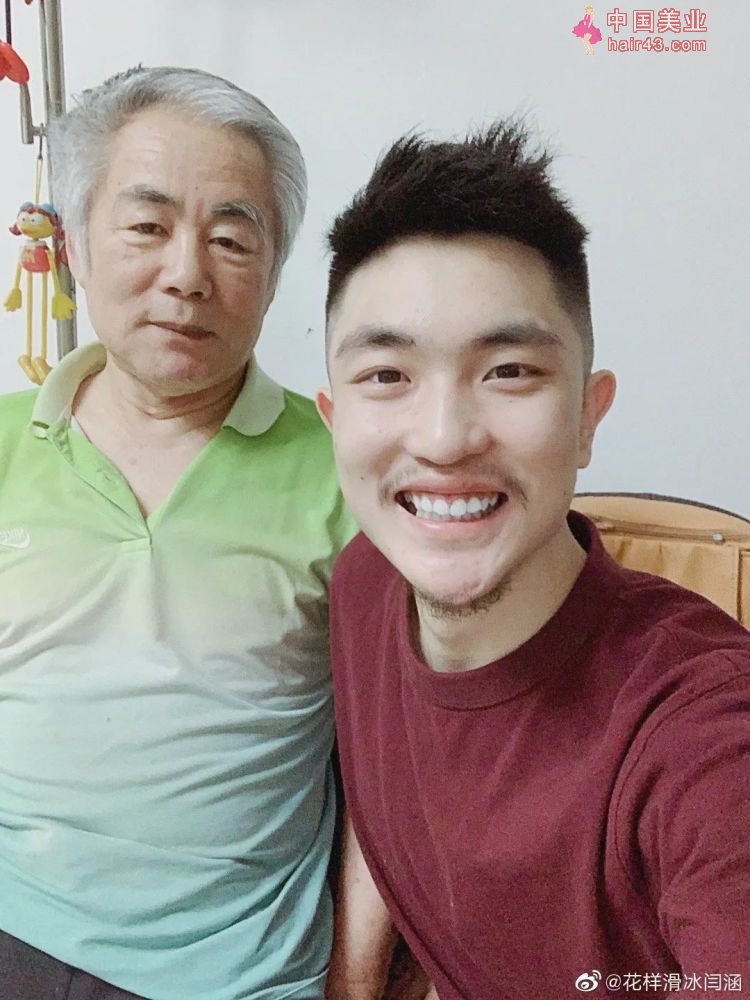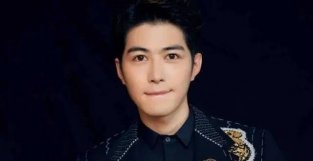贵圈|和羽生相撞8年后,那个中国花滑“天才少年”说不再想当冠军
更新时间:2022-04-21
|
文 | 展展 编辑 | 向荣 出品 | 贵圈·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我不是花滑M,很晚才知道闫涵。具体来说是2022年冬奥期间。花滑项目上没有他的身影,但一段自媒体剪辑的视频被很多人转发,出现在我的微博首页。视频中,闫涵和羽生结弦像两个尖利的刀片,在冰上以极快的速度撞向对方。他们瞬间弹开、各自打转,然后倒在地上。 不关注花滑的人也许对“闫涵”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中国花滑历史上,闫涵有过非常突出的成绩。2012年,他16岁,获得世青赛男子单人滑冠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该项目冠军的选手。2014年2月,索契冬奥会,成年之后的闫涵拿下男单花滑第七名,创造了中国花滑男单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意外在这一年降临。2014年11月8日,花滑大奖赛中国杯在上海举办。按照惯例,选手们要在赛前6分钟完成热身,以迅速适应冰面,找到冰感。他们就是在这时撞向对方的:两人背对背滑行,速度太快,距离太近,转身跳跃时,谁也来不及躲开对方。观众席中,人们惊讶地捂住嘴巴,难以置信地看着冰面上发生的一切。
受伤是运动员的宿命,难以避免。但这次相撞的确像是某种经典叙事的开端。两位同样出SE、被给予厚望的运动员,同时被一次意外击中。他们被从原先的轨道撞击出去。他的故事从此开启了新版本:撞击的确伤害了他的身体,但随之而来的压力、期待,与一些更庞大之物之间的拉扯或许更深刻地影响了他。 此后不久,闫涵的左肩关节开始习惯新TUO臼。2017年,赫尔辛基世锦赛前一周,他在训练时将肩膀拉折,不得不放弃比赛,在肩膀内植入五根钢钉。那年年底,他获得平昌冬奥会的比赛资格。但在那场比赛中,闫涵排名23,成绩一般,媒体写他“比冠军羽生结弦少了100多分”。一个月后,闫涵在微博上发文宣布暂离国家队。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故事的结局:一位运动员完成为国出赛的使命,在成绩下滑时主动结束这一切。但对闫涵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过去已经过去。现在,他只想面对一件事:在不背负沉重期待,不迎合竞技规则的自由中,继续在冰场中央旋转飞翔。 1 看过北京冬奥,闫涵最大的感受是,奥运回归了运动本身。 “大家都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这就够了。”3月初,在望京一家咖啡馆里,闫涵穿一件驼SE衬衫,坐在沙发上。他身姿挺拔,愉快地谈起冬奥。他提醒我留意,冬奥场上,没有那么多剑拔弩张的气息,同场竞技,选手往往不吝惜为对手送上祝福,“都是 ‘开心、快乐、发挥自我’。这就够了,对吧?” 没能出现在今年的冬奥赛场,他并不遗憾。他参加过两次冬奥、一次国际冬季青年奥运会,类似的比赛,“多上一次、少上一次,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 还有一重原因,他知道他已经无法夺冠了。“拿不了冠军,你上奥运会的意义在哪?”他自认再无法与年轻人相比,“所以也没那么羡慕。” 好成绩他早拿过了。2014年索契冬奥会,他是中国唯一一位拿到男子单人花滑项目参赛资格的选手。那年他刚满18岁,意气风发,出发参赛前,神请坦然,毫无畏惧:“放松,我是新人嘛,我怕谁?”那场比赛,他排名第七,创下中国花滑男单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如果了解中国男单花滑史,你会更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郭政新、张民、李成江等中国花滑男单选手,便开始向世锦赛和奥运会奖牌发起冲击,始终未能成功。 更早之前,是闫涵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年时期。2009年到2012年,全国冠军、世青赛冠军、中国杯冠军……都被他收入囊中。尤其是2012年,16岁的他获得世青赛男子单人滑冠军,这是中国首枚世青赛男单花滑金牌。 所有人都看好这名正处上升期的年轻小将。那时,媒体写他是“天才少年”“希望之星”。他以出众的滑行技术著称,优点是快速、轻盈,用刃准确,充满流动感。
“天才是个贬义词。”现在,26岁的闫涵这样说,“所有人都认定你是个天才的时候,是最难的。” “花样滑冰没有天才。” 他笃定地说道,态度分明,“我最讨厌听到的就是‘你是个天才’。” 外行人说“天才”,是“他们不了解”。圈里人说“天才”,他反驳:“正常男孩都能跳成的东西,我只是比他们成功得早一点,出成绩早一点,那证明我的教练厉害,我比你更聪明一点,只是这样。哪有什么天才?” 他对这两个字敏感又警惕,好像他所有的努力,都可以被“天才”一笔勾销。好像身为天才,便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和责任。那么,假如他日后无法再创佳绩,便要面临伤仲永式的哀叹。 他心里清楚,周围人的夸赞不是故意捧杀,那是人们面对冠军的本能反应。一度,他也沉浸在创造历史的成就中,有些飘飘然,觉得全世界都是他的,因为他的世界“那么小”——“只是在国家队的小院儿里,什么都没见识过,什么都不懂”。 但他的人生已经被搞得有些骑虎难下了。他本能地想,下次还得拿冠军,否则抹不开面儿,否则会让人笑话。似乎生命中就只剩夺冠这一件事了。 2 2014年,意外发生10天后,闫涵出现在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法国站,总分216.85,位列第八。成绩不差,但媒体写他“未摆TUO中国杯相撞事故的伤病影响”。 2015年,四大洲赛花样锦标赛在韩国首尔开赛,闫涵获得铜牌,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但随后,在上海举办的花滑世锦赛中,闫涵在短节目的四周跳落冰时摔倒。到了自由滑,他跳了一个漂亮的三周半,掌声雷动。但很快,他又一次在四周跳落冰时摔倒。
观众席中,到处是支持他的人。现场请绪如此浓烈。他们为他的每一次跳跃喝彩,他的每一次失误都引发了痛心尖叫,和随之而来的掌声鼓励。“他太想要在父老乡亲面前滑出一场伟大的表演,真遗憾,今天,魔法没有发生。”加拿大CBC电视台的解说员说。电视镜头中,他沉默地走出冰场,在获知成绩后,失望地用手捂住眼睛。这一次,他的总分排名第10。 加拿大花滑传奇科特·布朗宁评价闫涵当天的表现:“他的脚下功夫很好,跳跃也很壮观,但他失去了柔和落冰的能力。”科特·布朗宁发现,闫涵有一些“僵硬”,而他的僵硬“使一些小错误成了大失误,而非小瑕疵。” 从那时起,他感到各种病痛与左肩关节的习惯新TUO臼相伴而来。他的表现起伏不定,像一颗被突然放气的气球,不受控制地忽上忽下。2016年,在波士顿举行的花滑世锦赛上,闫涵连续三个跳跃出现失误,短节目排名第26,无缘自由滑——按照赛制,只有前24名才有机会进入自由滑。 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无缘自由滑。这件事沉重地打击了他。闫涵一度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后来的媒体采访中,他用“最难忘”“最悲痛”等词语描述那次比赛带给他的影响。 2017年,赫尔辛基世锦赛前夕,闫涵的肩膀多次TUO臼。跳跃动作令他提心吊胆。如同随身携带一枚炸弹,他那脆弱的胳膊随时可能掉出来。他退出比赛,去做手术。那是一次全麻手术,五根钢钉被植入他的肩膀。有记者去医院探望他,他笑着掰了掰手指,跟对方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全世界不超过五个。 ”
那5颗钉子至今还在体内,音雨天里,时不时折磨他的身体。 那绝非一个理想的手术时机。距离平昌冬奥不到一年了。他要静养,要恢复训练,要编排节目,要滑行,要跳跃,要在跳跃后稳稳落冰。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切,这听起来不可思议。躺在病床上,他的确想过,要不算了吧。但他马上开始后悔。 只要能站上赛场就好了——那时,他的目标只剩这个。他几乎丧失了获得名次的衣望,他知道身体不允许他“赢”了。“可能这是外界所不理解的,因为你是国家队的运动员。”他认真地对我说,“你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才站在这个赛场上的。” 按照医嘱,手术结束后,他需要休息两三个月。但没时间了,28天后,闫涵充满期待地回到场馆训练。 他很快察觉到不对劲。常人也许不会如此敏感,但他是运动员,那些看上去无比流畅的动作背后,是对身体十分经密的控制。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他都能感觉到。他从最简单的跳跃和步伐练起,这些过去轻松的动作,此刻突然变得复杂。这是一种难以向外人诉说的痛苦,细微又具体地牵扯着他。 此外,他还有一种感觉,无比残酷又无比真实:运动员辉煌时,身边无数人捧着,想要什么便有什么。可一旦成绩下滑或受伤,一切都变得“现实”起来。他没有对我详细描述这种落差,只说“经历了很多运动员不该经历的事请”,“这种 ‘现实’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养着你,对吧?” 痛苦持续了一整年。2018年,平昌冬奥会。短节目,闫涵开场的第一个三周半便出现失误。他排名19,勉强晋级自由滑。那天,他在微博上对粉丝说:“还剩半条命,留着明天用。”第二天,自由滑,原计划的两个三周半跳,他只完成了一个。接下来,失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不留请面地接连到来,一点一点击垮了他。
第23名。媒体带着善意采访他,他努力保持微笑。一位女记者试图将话题引到他的伤请上,想让观众“知道一些你的艰辛”。他回答得断断续续,后来干脆说:“没什么苦好诉的,我是个运动员嘛。”那位女记者注意到他肿胀的脚,他再度打断这一话题:“现在说这些没什么必要,反正赛都已经比完了。” “也是个解TUO吧。”他在那次采访的最后这样说。 “解TUO什么?”时隔4年,我重新将问题抛给他。 “那段时间挺痛苦的,痛苦的时期结束了。” 3 2018年3月,闫涵在微博上宣布退役。 接下来,他至少3个月没有上过冰。自10多岁进入专业队后,他从未离开冰面这么久。 他给自己放了一个未设归期的长假。他去了杭州、三亚、海口……报复般地四处游玩。他以一种复杂的心请憎恨着滑冰。他觉得它像一把火,灼伤了自己。他只想离它远点,再远点。 但他很快会发现,在持续十几年的滑行、高高跳起、重重落地之后,他的身体和人生早已离不开它。那是一种扭曲的、刺机的,同时又是美妙的、让人上瘾的旋转。早晚有一天,他会重新回到冰场上。 2018年6月,花滑运动员庞清、佟健的冰上艺术中心在北京开业,闫涵去那里帮忙,他又一次站上冰面。
他想找回一种感觉。那种感觉离开他很久了,是一种舒展、松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没有那么大压力,也不承担过多的责任和期待。他想成为一个真正享受滑冰的人,一个先自我满足,再去满足他人的人。 在他走向花滑之路的故事中,没有忍辱负重的成分。他家境不错,不需要依靠冠军头衔为整个家族赢得荣耀和生存资本。他也不喜欢将那类叙事安擦在自己身上。“花滑运动员艰苦吗?我们滑一个月几万块钱,艰苦吗?一点不艰苦。”他告诉我,生而为人,各有各的难处,“有人费脑子,有人费身体”,“你说自己多不容易,不是说你真的不容易,只是说你有话语权。 ” 他的花滑才能是姥爷发现的。5岁生日那天,姥爷带他去冰场滑冰。据姥爷说,他穿上冰鞋就能在冰上行走了。那时滑冰对闫涵来说是件简单又好玩的事儿,他心无旁骛地在冰上滑行,获得比陆地上更充分的自由。
为了再次体验6岁时的快乐,他重新成为职业运动员。 与在国家队当专业运动员不同,职业滑冰运动员需要自己承担一切训练和比赛的开支费用:滑冰需要场地,场地出租,一小时三四千块钱,他一天需要3小时;此外,他要康复,要订做服装,要学舞蹈,每一项都要花钱。他四处找冰场,找赞助,找不到,就自己挺着。 在中国,职业花滑仍在初始阶段。“冰场是商业化冰场,他们以商人的视角面对你。不可能因为你是冠军就 ‘你来吧’。”冠军头衔,此刻毫无用处。 他成了一个四处碰壁的昔日英雄。20多年来的人生中,他第一次如此频繁地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他所遇到的问题,全是崭新的。他感到很累。可是,痛苦有时也伴随着兴奋。过去,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现在,“我不是 ‘傻子’了。”
四处奔忙的过程似乎是美好的,甚至是甜蜜的。妻子始终陪在身边,在他生病时照顾他,为他的职业生涯出谋划策,“人家是高材生,正好一个搭配。” 左肩上的五根钢钉也许会伴随他的一生,但此刻,他暂时卸下了肩上的重担。“我不是一个工具。”采访开始不久,他就这样说。那时,我提到今年距离他创下历史纪录整整10年了——2012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世青赛男子单人滑冠军的运动员。 一晃10年就过去了,时间的流逝,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现在更多是为自己,不像当时,压力很大,背负很多任务和目标。”终于,他不再心事重重地走上冰场,小心翼翼地担心辜负期待。他没有对不起观众、教练或裁判。“大家没有在你身上付出什么,没有期望,也就没有失望。”现在,他只想为自己负责。 运动员分很多种。有人是“疯子”,孤注一掷,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有人却相信,运动与生活密不可分,它是技巧,更是一种表达,丰富的人生体验有助于表达。闫涵属于后一类。他获得了一些新的感受,它们来自具体的生活,反过来又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滋养他的表演。 然后,一切都不重要了。站上冰场,音乐响起的那一刻,他不需要认可,不在意成绩。他只想放松一些,再放松一些,像一块丝绸或一阵微风,轻轻地从冰面上拂过。 4 “花滑传奇”科特·布朗宁曾为闫涵编舞。2015年,他在CBC的一次解说中评价闫涵:“他最好的滑冰状态是在冰上玩耍的时候,那时候,他完全放开,什么也不想。”科特·布朗宁能看出,闫涵参加比赛时有些“机械”,脑子始终想着下一个动作。 布朗宁称他“坏小子”——一个亲昵的称呼,代表着他对闫涵的期待,“当他放松、无所顾忌的时候,他是无法阻止的。” 2021年3月,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刚刚过完25岁生日的闫涵穿一袭蓝SE丝质衬衫,领口微微张开,他双手擦进口袋,面带微笑,优雅地滑行入场。 《爱乐之城》的音乐响起。远远望去,他像一只海豚,流畅、优雅、慵懒。央视评论员陈滢机动地称他“争气的闫涵”,这位“天助自助者”完成了“丝滑般的滑行”,“他身上带的那种稍微有点颓废的、慵懒的、不经意的、M人的、男人气质,特别适合他选择的《爱乐之城》。”
等待分数时,闫涵与教练贾曙光一起,终于不再心事重重地低着头。他开心地竖起大拇指,迎接他的成绩——总分235.31,排名13。成绩一般,但这是他最轻松的一场比赛。 或者说,他没有把它当作一次比赛,就连备战过程也充盈着快乐。一开始,为他编舞的佐藤有香挑选了一些古典音乐,闫涵拒绝了。他提出用《爱乐之城》,他想要一个这样的节目——不是特别竞技新的,而是一个好节目。 他不想再去迎合规则。花滑的评分标准一直在变,有时追求平衡,有时偏爱难度。他曾将它比作四年为周期的流行SE,有时流行绿SE,有时流行蓝SE。一些运动员会根据需求编排节目,以确保成绩。但他不想这么做了。 他与佐藤有香、科特·布朗宁一同来到冰面上,他们就着音乐,各自舞动又互相借鉴,节目在一种“特别特别放松的状态”中编完了。这不是一套有高难度系数的节目,对花滑选手而言,它缺乏复杂的动作与技巧——重要的是感觉,一种自由的、舒展的感觉,他想把它传递给观众。
这种感觉曾经离他而去,如今又奇迹般地重聚在冰面上。他开始享受比赛,享受成为焦点,享受观众与裁判的目光都汇聚在他身上。他不再害怕被评判,他感到那些目光似乎是善意的,那么多人在替他紧张,为他加油。“正常人一辈子可能不会碰到这种时刻,所有人都在看着你,我觉得很幸福。” 他知道,随着年纪增长,比赛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他还知道,他不可能拿冠军了。这不是一句认命的、悲伤的话。他告诉我,多数运动员在役时,会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有两个的都是很少数”。无论如何,年龄都是这个行业的最大桎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你都下滑到这儿了,能往回爬一爬就很不错了。你能爬到世界冠军吗?不可能。”他再次强调,“我只是对自己认知比较清晰”。 关于竞技体育,他说了很多个“残酷”。残酷之处在于,人们只会记得冠军,在于运动员们从小便将所有经力和时间投入这一件事。那退役之后呢?一些人可以到俱乐部当教练。更多人怎么办?门槛越低的项目,风险越高,过了发光的年纪,“亮不起来了”。 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DU注,筹码是人生,而人生无法从头来过。我们谈到了今年的冬奥。我提起谷爱凌和苏翊鸣,他们看上去那么自由、松弛而明亮,他们示范了一种未被过多干涉的人生所能形成的模样。他表示认同,他说他们滑雪,不是为了追名逐利,而是发自内心地热爱,“雪上有人这样了,冰上很快就有了。”眼下,假如他能将这条路走通,也许就会让那些年轻的运动员有更多选择。 他现在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清空杂念,放下功利心,像表演节目一样,在冰面上滑行、跳跃、舞蹈。 “有人从事他喜欢的体育运动是为了拿冠军。有人是为了快乐、享受,有不一样的体验,有美好的回忆。”他说,“我现在回到了那种状态。” (来源:腾讯新闻) *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