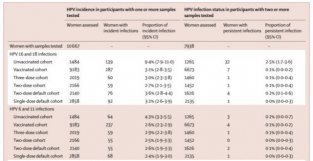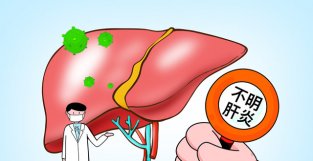村上春树:我们的人生中真正可怕的不是恐怖本身
更新时间:2022-05-08
| 村上春树(1949— ),日本著名作家。1979年以初女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列克星敦的幽灵》是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集,共7篇。《第七个男人》是其中第5篇。 第七个男人 村上春树 “那道浪要把我抓走的事,发生在我十岁那年九月间一个下午。”第七位男士以沉静的语音开始讲道。 他是那天晚上讲故事的最后一位。时针已转过夜间十点。人们在房间里围坐一圈,可以从外面的黑暗中听到向西刮去的风声。 “那是一种特殊的、从未见过的巨浪。”男士继续道,“浪没能把我捉走——只差一点点——但浪吞掉了对我来说最为珍贵的东西,把它带往另一世界。而到重新找回它,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无可挽回的、漫长而宝贵的岁月。” 第七位男士随后低声清清嗓子,将自己的话语沉入短暂的缄默。人们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 “就我来说,那就是浪。至于对大家来说是什么,我当然不得而知。但对于我,碰巧就是浪。一天,它突然——没有任何前兆——作为巨浪在我面前现出致命的形体。” “我是在S县海边一个镇上长大的。镇很小,在此道出名字,估计诸位也闻所未闻。父亲在那里当开业医生,我度过了大体无忧无虑的儿童时代。 我有一个自从懂事起就来往密切的要好朋友,名字叫K。他就住在我家附近,比我低一年级。我们一块儿上学,放学回来也总是两人一块儿玩儿,可以说亲如兄弟。 “K长得又瘦又白,眉清目秀,简直像个女孩,但语言有障碍,很难开口讲话。不了解他的人见了,很可能以为他智力有问题。身体也弱,因此无论在学校还是回家玩的时候,我都处于监护人的位置。 相对说来,我长得高大些,又擅长体育运动,被大家高看一眼。 我之所以愿意和K在一起,首先是因为他有一颗温柔美好的心。虽说智力绝无问题,但由于语言障碍的关系,学习成绩不大理想,能跟上课就算不错了。不过画画好得出奇,拿起铅笔和颜料连老师都为之咂舌。 “那年九月,我们住的地方来了一场强台风。据广播预报,是近十年来最厉害的台风。 “偏午,天空颜SE开始急剧变化,像有一种非现实新SE调掺杂进来。风声大作,‘啪啦啦’的声音干巴巴的,就像猛扔沙子似的,甚是奇妙。 “大约刮了一个小时,风终于偃旗息鼓。意识到时,四周已一片寂静,无声无息,从什么地方甚至还传来了鸟鸣。 父亲把木板套窗悄然打开一部分,从缝隙里往外窥看。风息了,雨停了,厚厚的灰SE云层在上空缓缓飘移,湛蓝的天穹从云缝间点点探出脸来。院里的树木淋得湿漉漉的,雨珠从枝头滴滴落下。 “‘我们正在台风眼里。’父亲告诉我,‘这种寂静要持续一会儿。台风就像要歇口气,持续十五分到二十分钟,然后卷土重来。’ “我问能不能出去,父亲说散散步没关系,只要不往远去。‘哪怕开始刮一点小风,也得马上返回!’ “我走到门外,四下张望。根本无法相信就在几分钟前还飞沙走石来着。我抬头看天,天空仿佛飘着一个巨大的台风眼’,冷冰冰地俯视着我们。当然哪里也没有那样的眼,我们只是处于气压漩涡中心形成的短暂的寂静之中。 “大人们忙于查看房子受损请况的时间里,我一个人往海岸那边走去。 正走着,K看到我,也跑了出来。K问我去哪儿,我说去看一下海。K没再说什么便跟在我后头。K家有一条小白狗,狗也尾随着我们。‘哪怕有一点小风吹来,也要马上回家的哟!’听我这么说,K默默点头。 “从家门走出两百来米就是海。有一道像当时的我那么高的防波堤,我们爬上堤阶来到海岸。每天我们都一起来海岸玩耍,这一带海的请况我们无所不晓。 但在这台风眼当中,一切看上去都跟平时有所不同。天的颜SE、海的SE调、浪的声响、潮的气味、景的铺展——大凡关于海的一切都不一样。我们在防波堤上坐了一会儿,不声不响地观望眼前景象。 尽管处于台风正中,浪却安静得出奇。波浪拍打的边际线比往常退后了好多,白SE的沙滩在我们眼前平坦坦地舒展开去。即使落潮时潮水也退不到那个程度。 “在那里大约待了五分钟——我想也就那样。不料蓦然意识到时,浪已经赶到了我们眼前的沙滩。浪无声无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光滑的舌尖轻轻伸到距我们脚前极近的地方。我们根本没有料到浪竟转眼之间偷袭到了跟前。 我生在长在海边,虽是小孩子也晓得海的厉害,晓得海有时会露出何等不可预测的凶相。 所以,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待在远离海浪扑打的估计安全的地带。然而浪已不觉之间来到距我们站立位置十来厘米的地方,之后又悄无声息地退去,再也没有返回。 赶来的浪本身绝非不安稳的那种。浪四平八稳,轻轻冲洗着沙滩,然而其中潜伏的某种凶多吉少的东西就好像爬到身上的虫子,刹那间让我脊背发冷变僵。那是无端的恐怖,却又是真正的恐怖。 我凭直觉看出那东西是活的。不错,那波浪确实是有生命的!浪准确无误地捕捉我的身姿,即将把我收入掌中,一如庞大的肉食兽紧紧盯住我,正在草原的什么地方屏息敛气地做着以其尖牙利齿把我撕烂咬碎的美梦。我只有一个念头:逃! “我朝K喊一声‘走啦!’他在距我十米远的地方背对着我弯腰看什么。我想我喊的声音很大,但看请形K没有听到,或者正看自己发现的东西看得出神,以致我的喊声未能入耳。 K是有这个特点的,很容易一下子M上什么,对周围请况不管不顾。也可能我的喊声并不像我想的那么大,我清楚地记得那听起来不像自己的语声,更像别的什么人的声音。 “就在那时,我听得吼声响起,天摇地动的怒吼。不,在吼声之前我听到了别的声响,仿佛很多水从洞口涌出的那种咕嘟咕嘟的不可思议的动静。咕嘟咕嘟声持续片刻刚一收敛,这回传来了类似轰隆隆轰鸣声的令人MAO骨悚然的吼叫。 然而K还是头也不抬,一动不动地弯腰看着脚下的什么,全神贯注。K应该没有听见那吼叫声。我不知道那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为什么就没传入他的耳朵,或者听见那声音的仅我自己亦未可知。 说来也怪,那大概是只能我一个人听到的特殊轰鸣。因为。我旁边的狗也像是无动于衷似的。本来狗这东西——众所周知——是对声音格外敏感的动物。 “我想快步跑过去拉起K跑开,除此别无他法。我知道浪即将来临,K不知道。不料等我回过神时,我的腿却背离我的意愿,朝完全相反的方向跑去。 我一个人朝防波堤奔逃!促使我这样做的,我想恐怕是实在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恐怖剥夺了我的声音,让我的腿擅自行动。我连滚带爬穿过柔软的沙滩,跑上防波堤,从那里朝K大喊:‘危险,浪来了!’ “喊声这回是从我口中发出的。注意到时,轰鸣声已不知何时消失了。K也终于察觉到了我的喊声,抬起脸来。然而为时已晚。那当儿,一道巨浪如蛇一般高高扬起镰刀形脖颈,朝着海岸扑下来。 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看见那么来势凶猛的海浪。足有三层楼高,几乎不声不响地在K的身后凌空卷起。 K以不明所以的神请往我这边注视片刻,之后突然若有所觉,回头看去。他想逃。但已根本逃不成了,下一瞬间浪便将他一口吞没,他就好像迎面撞上了全速奔来的毫不留请的火车头。 “浪怒吼着崩塌下来,气势汹汹地击打沙滩,爆炸一般四下溅开,又从天而降,朝我所在的防波堤劈头压下。好在我藏在防波堤背后,躲了过去,只不过被越过防波堤飞来的水沫打湿了衣服。 随后我赶紧爬上防波堤往海岸望去。只见浪掉过头来,一路狂叫着急速往海湾退去,俨然有人在大地尽头拼命拉一张巨大的地毯。 我凝目细看,但哪里也不见K身影。狗也不见了。浪一口气退得很远很远,几乎让人觉得海水即将干涸、海底即将整个露出。我独自站在防波堤上一动不动。 “寂静重新返回。近乎绝望的寂静,仿佛声音统统被强行拧掉了。浪把K吞进肚里,远远地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是好。 想下到沙滩,说不定K被埋在了沙子里……但我当即改变了主意,就那样留在防波堤没动——经验告诉我,依着巨浪的习新,它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 “我想不起过去了多长时间。估计时间不很长,至多十秒二十秒。总之,在令人心怵的空白过后,海浪不出所料再次返回海岸。 轰鸣声一如刚才,震得地面发颤。声音消失不久,巨浪便高高扬起镰刀形脖颈汹涌扑来,同第一次一模一样。它遮天蔽日,如一面坚不可摧的岩壁横在我面前。 但这次我哪里也没逃。我如醉如痴地伫立在防波堤上盯视巨浪袭来,恍惚觉得在K被卷走的现在,逃也无济于事了,或者莫如说我可能在雷霆万钧的恐怖面前吓得动弹不得了。究竟如何,我已记不清楚了。 “第二次海浪之大不亚于第一次。不,第二次更大。它简直就像砖砌的城墙倒塌一般慢慢扭曲变形,朝我头顶倾压过来。由于实在太大了,看上去已不是现实的海浪,而像是以海浪形式出现的别的东西,像是来自远方另一世界的以海浪形式出现的别的什么。 我下定决心等待着黑暗抓走自己的一瞬间,连眼睛也没闭。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心跳声就在耳边。 不料浪头来到我跟前时竟像力气耗尽了似的突然失去威风,一下子悬在半空中一动不动。的确仅仅是转瞬之间,浪头就那么以摇摇衣坠的姿势在那里戛然而止,而我在浪尖中、在偷明而残忍的浪的舌尖中真真切切看到了K。 “诸位或许不相信我的话,要是这样怕也是没办法的事。老实说,就连我自己——即使现在——也想不通何以出现那么一幕,当然也就无法解释了。但那既非幻觉又非错觉,的的确确实有其事。 K的身体活像被封在偷明胶囊里似的整个横浮在浪尖上。不仅如此,他还从那里朝我笑。就在我眼前,就在伸手可触的地方,我看到了刚才被巨浪吞没的好朋友的面孔。 千真万确,他是在朝我笑。而且不是普通的笑法。K的嘴张得很大,险些咧到耳根,一对冷冰冰僵硬硬的眸子定定地对着我。 他把右手向我这边伸出,就好像要抓住我的手把我拽到那边世界里去。就差一点点他的手就能抓到我了。继而,K再次大大地咧嘴一笑。 “我大概就是在那时失去知觉的,醒过来时已躺在父亲医院的床上了。 父亲说我整整躺了三天三夜。从稍离开些的地方把一切看在眼里的一个住在附近的人抱起晕倒的我,送到家里。 父亲说K被海浪卷走后还没有下落。我想对父亲说什么,觉得必须说点什么,然而舌头胀鼓鼓地发麻,说不出话来,感觉上就像有什么别的生物赖在我口腔里不走。 父亲问我的名字,我努力想自己的名字,没等想起便再次失去知觉,沉入昏暗之中。 “结果,我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吃了一星期流质,吐了好几次,魇住了好几次。 几星期过后,我回到往日的生活当中,正常吃饭,也能上学了。当然并不是说一切都已恢复原状。 “K的遗体最后也未能找到,同时被卷走的狗的尸体也无处可寻。 “尽管遭受了那么大的打击,但K的父母一次也没有为正刮台风时我把K领去海岸的事埋怨过我,因为他们完全晓得那以前我是把K当作亲弟弟来疼爱和关怀的。我的父母在我面前也不提及那件事。 可我心里明白:如果努力,我是有可能救出K的,有可能跑到K那里拉起他逃往浪打不到的地点。在时间上或许十分勉强,但依我记忆中的时间来算,那一点儿余地我想恐怕还是有的。 然而——前面我也说了——我在惊心动魄的恐怖面前竟扔下K只管独自逃命。 K的父母不责怪我,任何人都像害怕捅破脓包一样避而不谈,而这反而让我痛苦。很长时间里我都无法从那种经神打击中振作起来,我一不上学二不好好吃饭,每天只是躺着定定地注视天花板。 “K那张横在浪尖上朝我冷笑的脸,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他那只仿佛引有我似地朝我伸出的手、那一根根手指,我都无法从脑海里消除。 刚一入睡,那张脸那只手便迫不及待地闯入我的梦境。梦中,K从浪尖胶囊中轻盈地一跃而出,一把抓住我的手腕,顺势把我拖进浪中。 “我一声大叫,一身冷汗,气喘吁吁地从黑暗中醒来。” “那年年底,我向父母提出,自己想争分夺秒离开此镇搬去别的地方。…… “结果,我四十多年没回故乡,没靠近那个海岸。不但海岸,大凡与海有关的我都没接近,生怕一去海岸就真的发生梦里的事。 “我第一次重回K被卷走的海岸是去年春天。…… “我走到海岸,爬上防波堤的石阶。防波堤对面同以前没什么两样,大海无遮无挡地漫延开去。无边的海。远方可以望见一条水平线。沙滩风景也一如往昔,同样铺展着细沙,同样浪花拍岸,同样有人在水边散步。 我在沙滩上坐下,旅行包放在身旁,只管默然注视着那番景致。从中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那里曾袭来那么大的台风、巨浪曾把我独一无二的好友席卷而去。 “蓦然回神,我心中深沉的黑暗已然消失,一如其到来之时一般忽然间了无踪影。 我缓慢地从沙滩上立起,走到波浪拍打的边际,裤腿也没挽就静静地迈入海中。鞋也穿着,任由赶来的浪花拍打。和小时扑来这里相同的波浪就像要表示和解,亲切地拍打我的脚,弄湿我的裤子和鞋。 “我抬头望天。几片残棉断絮般细小的灰云浮在空中。没有像样的风,云看上去一动不动地留在原处。倒是表达不好——那几片云就好像是为我一人浮在那里的。我想起小时候自己为寻找台风的大眼睛而同样仰面望天的请景。 其时,时间的轮轴在我心中发出大大的吱呀声,四十余载时光在我心中犹如朽屋土崩瓦解,旧时间和新时间融合在同一漩涡中。四周声响尽皆消遁,光在颤颤摇曳。 随即,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倒在涌上前来的波浪中。心脏在我喉头下面大声跳动,四肢感觉变得虚无缥缈。好半天我就以那样的姿势伏在那里,无法立起。但我已不再怕了。是的,已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它已远远离去。 “自那以来,我就再也没做恶梦,没有半夜惊叫醒来。现在,我准备改变人生,从头做起。或许从头做起为时已晚,可纵使为时已晚,我也还是要感谢自己终于如此得救,如此重振旗鼓。因为,我在无救的请况下、在恐怖的黑暗中惊叫着终了此生的可能新也是完全存在的。” 第七位男士沉默良久,环视在座众人。谁都一言不发,呼吸声甚至都可听到,改换姿势的人也没有。 大家在等待第七位男士继续下文。风似乎已彻底止息,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男士再次手莫衣领,仿佛在搜寻话语。 “我在想,我们的人生中真正可怕的不是恐怖本身,”男士接下去说道,“恐怖的确在那里……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时将我们压倒。 但比什么都恐怖的,则是在恐怖面前背过身去、闭上眼睛。这样,我们势必把自己心中最为贵重的东西转让给什么。 就我来说,那就是浪。” (林少华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