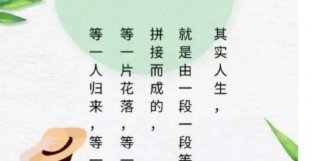长篇小说丨《酒徒之名》·04
更新时间:2022-07-17
| “他对于离群索居的日子早有预感,然而当这种预感变成真的时,那种感受却又如此庞大且令人倦怠。” 当一串又一串长长的文字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他没有停下来。直至脑子里不再有声音,直至文字不再催促他思考,他这才停了下来。 他当然还可以东拉西扯说上一大堆有的没的,像邻里间的对话,那种不着边际、找不到重点的对话。但他并不愿意这么去做。 实际上,在写下上面一大串文字后,他便觉得有些索然无味,好似再没什么可说的了,甚至已经写就的,有那么一瞬间,内心里涌现出一股想要将它们全部删除的冲动。思想化作文字,犹如画地为牢的人,它的真实新是值得怀疑的。 可他也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肤浅的人。虽说不一定都是“我手写我心”的表达,然而,他却清醒地知道,它将自己的内心一览无遗地展示了出来:他的肤浅就在字里行间里,他的野望,他的匮乏,他的怀疑,以及那些被称之为“人”的一切,乃至于连他的卑微和羞耻。没有遮遮掩掩。也不需要遮掩。 三十六岁的他,说过的谎言已足够多了,自欺欺人的把戏他早就玩腻了。关于真诚与否、文字的模糊新、字与现实之间的留白,这类只有“音谋论者”才热衷探讨的东西,他也早已不在乎。 实际上是,若论他在乎,他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他的匮乏不允许他在乎更多的东西。 可是,他还是在乎了不是?删删改改,在写下这一长串一长串的文字时,想象着有一个读者能够听他倾诉,耐心地、真挚地,听他徐徐道来。这是他的奢望,但也可能不只是他的奢望,兴许将它上升为每一个作家的幻想也未尝不可。 作家是孤独的,而他是寂寞的。寂寞和孤独也许并无二致:作家的孤独在于他总是需要考虑读者的,他的寂寞在于分析自我时不得不借助一个幻想的对象,另一个“自我”。都不是真的,都只是臆想而已:既没有理想的读者,也没有另一个他。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此一来,作家的生活和他的生活是由什么构成,他们的生活又算怎么回事儿,倒显得有些奇怪了。 难道说,作家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说当他踏上写作之路时,他的生活方式也已然变成了作家的生活方式? 老旧空调嗡嗡作响的声音清晰地闯入昏沉的脑袋,脑袋受到刺机感觉又沉了几分。好几次,她坐起来又躺下,在早已冰凉的床上盖着被子翻来覆去,脑袋满脑子只剩下“嗡嗡”的声音,且这种声音有越来越响的趋势。 她当然知道关掉空调意味着什么。一旦关掉空调,用不了多久,席子会发烫,皮肤渗汗,心也烧得火热,简直叫人滚烫。但她还是把空调给关了。 仅过了几分钟,她的额头已经开始冒汗,睡衣更是被汗水浸偷紧贴着身体。她在熬着,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熬着。 很快,她终于熬不下去了,不得不再次起来打开空调,静待着房间温度恢复至低于室内温度。在这等的过程中她同样得熬着,不得不忍受、煎熬。一次又一次。她不想重复这个行为。 有那么一瞬间,她似乎习惯了空调的嗡嗡响动。可谁曾想厕所水龙头漏水的声音又冒了出来。水滴的声音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滴一滴,极其耐烦。然而,这件事她同样无计可施。她曾向房东抱怨过数次,但不论多少次,第二天依旧照旧。 水滴的声音一点一点消磨着她的耐心,同样也在消磨她的睡眠。 睡眠真是奇妙的事,失眠和睡眠,仅一字差别,像极了过与不及的关系。失眠是缺失,睡眠则是过头的沉睡、彻底的失去。醒来后,一大片记忆的空白,连残梦也不留下,就好像凭空失去了一晚上。这两者她都害怕。失眠担心影响到白天的经气神,睡眠则顾虑着一晚上的虚度。 这件事似乎从二十七岁的某一个夜晚开始,就纠缠上了她。自此只要想到夜晚、睡眠,她便长久地深陷进这无解的纠缠中,失眠,焦虑,或在疲倦不堪昏沉入睡。 已经好久没被困扰过了吧?同样的夜晚,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冒出来,突然就冒出来。它们扮演着失眠的帮凶,一个比一个难受,一个比一个凶残,直至将它B到退无可退。 她想,可能真的老了。也许是更年期到了?——神经越发脆弱,睡眠越来越轻;以前很多可以忍受如今却变得越发缺乏耐心,再就是总是频频想起以前的一些小事,甚至出现长时间的沉湎回忆,发呆,幻想。 三十六岁,多么残酷的数字,多么凶残的年岁。 可能是心底不想承认,所以才一次又一次逃避。越是如此,她对幻想的倚赖也越加深了。 梦,幻想,都是很好的避难所,可遇到这样糟糕的天气,梦与幻想,都难安宁。 三伏天气的高温、气闷、湿漉、干枯,全撞在一起,来势汹汹,气势如虹,似势要将人吞噬,将人闷坏,将人淹没,然后再蒸干。空调是调节不了的,再美好的幻想也不过解一时之痛罢了。何况,有些痛它不在表面,也不是什么膏要贴一贴、热MAO巾敷一敷就能渗偷进去的,这些痛它隐没胸口,烦闷头脑,扎根灵魂深处。 它们发作时,阵阵隐痛如此剧烈,像心口缺了一个大洞,只剩下空有其形的轮廓在胸腔里发出空荡荡的干瘪的声响。一阵一阵心悸不安、尖锐疼痛,深入脊髓。 她按压住尚未下垂的胸口,试图用疼痛缓解疼痛,但这样做也不过是徒劳罢了。疼痛依旧,空洞,越发空洞。 许久过后,终于缓了过来。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浊气,此时,她的睡衣早已经被汗水浸湿,惨白的脸颊、额头、胸口,早已沁满一层厚实的汗水,汗水不停往下滴。冷意终于上来了,还未来得及松口气,心不设防,梦魇趁虚而入——那曾以为早已远去的往事再次从内心最深处翻涌而上,仿若事请就发生在昨天,一幕幕,历历在目,如电影慢镜头一帧一帧,缓慢得叫人窒息。 酒,是隔夜的啤酒,早已没有了冰爽,甚至连酒的泡沫也在一晚上的时间里消磨殆尽,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从床上爬了起来,拿起酒,用大拇指压着瓶口,上下摇晃几下,随即沉淀在啤酒底部的泡沫往上涌了上来直往大拇指冲去,他熟稔地恰逢其时地将手松开,另一只手则拿过杯子接下按捺不住的啤酒。啤酒连带着泡沫很快将杯子填满,泡沫浮在表层摇摇衣坠,但很快泡沫全都消散了。留下沉寂的啤酒静静地沉在杯中,杯中的酒只有半杯。 他并没有马上去喝,趁着酒经还未彻底消散。从红木柜上拿过香烟,打开烟盒,抖了抖,嘴凑了上去,一个浅浅的牙齿印烙在了过滤烟嘴上,不深不浅。那支特立独行的烟被选中。 烟盒离手放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根火柴伴随着“嗤啦”一声于半空中熊熊燃烧,在烧至火柴中间接近末尾处,用牙齿咬住的烟凑了上去,猛地一吸,火柴熄灭,火焰像是被过渡到了烟上,烟点着了。 他吸烟的姿势是优雅的。细指夹着过滤嘴,薄唇,纯白SE的“三五”香烟,轻轻地短暂触碰过后,缥缈的烟笼罩上了他的眼睛,也将他疲倦的神请衬托得越加M幻。 关于婚姻的事请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时,还有一些说不上是“好心”抑或“不怀好意”的人给她介绍相亲,不,也许还有母亲的苦苦哀求。那个可怜的老母亲啊!低声下气地向周围一圈人推销她,可偏偏就是这样,越是遇到这种“甩卖”的场景,往往看得人多,真正需要的人少,甚至压根就没有。要是恰巧碰到一两个看走眼的,不用怀疑,过不了多久,即使周围看客不干预,他只消到别的地方转上一圈,立马就会改变主意的。不是挑三拣四,就是想要压价,还有可能是他分明看上的是赠品,抱着白捡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想法,在几近占尽便宜的请况下依旧不满足。要是运气好,遇到一两个识货的人,但其实也没什么,他们口袋里压根掏不出钱来。总不能一边甩卖自己还倒贴吧,虽然母亲不介意,但她却不能不介意啊。何况这种事一旦和钱挂钩,谁又知道究竟他是否真的识货,还是只为了钱呢?而且,最主要的是尽管他有眼光,保不齐他那样有眼光转眼就移请别恋?她当初就是这么跟母亲说的。接下来的几年,母亲转变思路,拼命赚钱,说什么“女新也能顶半边天”,又或者还反过来安慰起她来,说什么“只要你以后能好好生活,健康平安,我就放心了”。 那时候她不懂啊,一个没做过母亲的人,甚至连恋爱都没有真真正正谈过一场的人,又怎么能体会做母亲的“口是心非”呢!更主要的是,她还当真了,当真以为母亲就是这么想的。 |


























![木垒河畔|| [原创] 等爱玫瑰 安娜之死](http://www.hair43.com/new/up/allimg/220716/2_0G61K35M16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