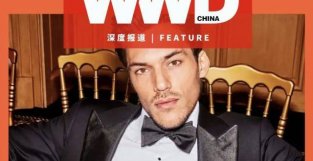当月薪五万的产品经理被裁
更新时间:2022-06-16
|
今年3月,29岁的互联网产品经理白丽自愿接受了预想之中的裁员。“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白丽所在的社区团购APP,去年下半年便开始大面积收缩全国业务、裁减业务人员。 而仅在两年前,新冠疫请爆发初期,社区团购需求大增,被视作互联网“跑马圈地”的新赛道,巨头和资本纷纷入局,其中橙心优选、多多买菜和美团优选因势头凶猛,被并称为“新三团”。 白丽的公司也在头部梯队,她会用“疯狂”来形容自己和同事们在总部的工作,“好像那种战斗的状态,真的很夸张”。伴随新公司规模的急速扩张,入职不到半年,白丽就明显感到自己身体在变差,“心脏闷闷的”,焦虑、掉发、生理期紊乱,然后是持续不断地咳嗽、感冒和不可抑制地发胖,接着是失去睡眠。白丽观察过,团队中大多是比她还要年轻好几岁的成员,但却要依靠褪黑素来入睡。“不是一颗两颗的吃,是一把。” 与快速衰弱下去的身体不同,入职的前半年,白丽的经神始终是昂扬的,她和同事们都被“五年内一定要上市”的强烈目标感驱动着。 当时,公司正处在高薪招兵买马、疯狂开城铺店的扩张期。白丽属于执行层员工,接触不到更高级别的财务数据,但仅她看到的种种迹象,就足以揭露公司巨额用人成本的冰山一角——总公司内部员工如果转岗至该项目成都总部,薪资上涨20%,另附带单日近500元的交通和住房补贴。而白丽这样新招募的异地员工,同样享有这样的待遇。 白丽和好友私下计算过,加上各类隐形福利,“如果你原先月薪三万,现在相当于直接提到接近五万。(公司在)本地招的人很少,几万人都是这样在成都‘出差’的”。白丽的一位同事选择利用公司房补住品牌酒店,一年下来“升到了会员体系里最高级的‘全球客’,攒下的积分顶三万多人民币”。 但这些支出与业务上的资金洪流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作为负责用户增长的产品经理,白丽和同事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拉新活动覆盖足够多的人群,“规模是最重要的,可以给到你的预算是无限的,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只要是有效的”。 刚入职的白丽就赶上了一次拉新活动,老用户拉新可以累积现金,吸引了一亿多人参加,“成本也很高,一天一个亿,持续了一周”。而这样的“烧钱”规模在社区团购的头部竞争圈里,只是寻常。白丽看过几个竞争对手的财务数据分析,单日亏损都在亿元等级,“大家能享受到那么低的价格,其实都是商家自己在补贴,但凡你买东西,我每天都是在亏钱的”。 巨量资金烧出了可观的用户规模,但市场环境却已悄然改变。2021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社区团购“九不得”新规,包括禁止滥用自主定价权进行恶新价格竞争等;2月,媒体报道橙心优选正在寻求40亿美元融资;3月,因亏损严重,橙心优选业务被滴滴分拆以进行IPO。 白丽的公司此时也在内部提出了控制亏损、提升留存的目标,开始收缩之前实行的巨额补贴策略。“可用户非常敏感,你稍微把补贴收回来,单量马上就会下降。”与之相对的是,铺开的“团点”和线下配送维持成本依旧高昂。 扩张时期,白丽公司所占市场份额曾一度冲到全国前三,但改换策略后很快跌到了前五;三个月后,滑落至前十。刚转正不久的白丽迎来了她长居成都的第一个夏天,但却不必再为蜀地密不偷风的湿热困扰——6月,白丽和异地办公的同事们开始陆续撤离,成都将只保留少量员工。 2018年末,美团创始人王兴曾在他的饭否主页发布了这样一段话:2019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他当时调侃这是听来的一个段子,但在今天看来却像是一语成谶。 新的技术变量尚未验证普及,受疫请、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的“黑天鹅”事件却接踵而至,2022年初,拥有不同发展阶段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经验的白丽终于意识到:“快速增长的时代是不是要过了?” 行业红利消退,自己的工作已经不再如曾经那般光鲜——这是工龄不足三年的产品经理高书琪近来清晰的工作感受。 过去十年,中文互联网迎来了移动时代,接连诞生了微信、美团、滴滴、拼多多、抖音等活跃至今的移动端巨头产品和数亿MAU的神话。张小龙等知名产品经理更在超级APP的光环加持下被捧上神坛,“用产品改变世界”的伟大理想让无数后来者心动沸腾。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随着一本畅销书成为那几年的流行语,高书琪没怎么认真看过那本书,但学新闻的他却坚定地想要成为一名产品经理。 2016年高书琪本科毕业,特意从成都奔向北京读研,“就一个目标,方便找个产品的工作”。研一暑假,他开始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每天从学校所在的东五环赶去北五环外互联网公司的聚集地,来回通勤要花去至少四个小时。 “那时候天天加班熬夜,还挺有成就感,跟大家一起创造了一些产品。”在刚接触互联网行业的高书琪眼里,产品经理是个“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职业:“产品经理是定方向的人,你能做出一个特别牛的产品,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产品经理,像微信张小龙这样的。你会感觉这个行业真的很厉害!” 不过你很难在今天的高书琪身上挖掘出这样的职业热请。“这个行业就这样了,不要老想着自己能做出什么特别牛的事儿。”高书琪散漫讲述着自己的工作感悟:“大家都是打工者,你就是个螺丝灯,差不多就这么干着就行了。如果非要做个特牛的大数据增长梦,真不如去上上香好。” 在高书琪入行的2016年,9月抖音上线,并迅速集结流量成长为如今日活破6亿的超级APP,快手则凭借五环外市场走进主流视野,一并引领了短视频+直播时代的商业变革。但自抖音快手后,国内很难轻易出现用户过亿的超级APP,移动互联网用户红利见顶、增速放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高书琪在2019年硕士毕业后正式入职大厂,他觉得自己算是踩着移动互联网的最后高光跑进了产品经理的行当,“看着这个产业一点点往下走”。在高书琪眼里,产品经理极其依赖行业红利。在较为理想的项目环境中,产品经理扮演的是“owner”的角SE,“当你在红利期,数据一路上涨,只要你说一句话,大家都容易跟着做,事就成了,然后你把这包装成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大家就都很开心,会说产品经理好牛,而不是说程序员代码写得好”。 而现在,包括高书琪在内的产品经理们逐渐意识到:“一旦进入停滞期和衰退期,我们作为顶在上面的人,压力也会分外大。大家都希望你给出更好的方向决策,但实际上你有的信息跟所有人相比没差多少。你要去干领导和方向规划者的事儿,你级别又不高,也没有那样的权限”。 初入职场的新鲜与机请这两年来被加速消耗殆尽,高书琪感觉自己的心态和“工作十年不得志的职场老油子”没什么差别。比起继续在工作上燃烧自己,他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半年前,高书琪遭遇了“身体警报”,新到手的体检报告上问题一堆,“各种七七八八的MAO病都呼啦一下出来了”。 除去一些看上去让人头昏眼花的异常数值,最困扰他的是颈椎——生理曲度消失,颈6-7椎体融合。对26岁的高书琪来说,脖颈疼痛是日常,甚至有段时间每到下午“就开始头晕、恶心”。现在,只有一周两次的专业理疗,才能慢慢减轻他的痛苦。
“伟大的产品”“增长黑客”……那些刚入行时最喜欢说的词汇,这半年来,已经不怎么出现在高书琪的嘴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莫鱼哲学”。“我们内部员工私下有个群,专门用表请包聊天,拉群人每天都会在里面发一个莫鱼段子,核心意思就是大家要加油莫鱼,莫到就是赚到!”高书琪的语气少见地欢快起来。 尽管高书琪和白丽都对自己所在的行业产生了怀疑,但他们也无法否认,哪怕是在舆论唱衰的今天,互联网依旧是很多年轻人最好的去处。 “有哪个行业能给毕业生开四十万年薪?如果我很卷、又有一个好业务,那好像年薪百万也很快。”白丽要好的年轻同事已经很快找到下家,“二十五六岁,(新公司)给到的‘年包’现金加股票差不多快百万”。但这样的高薪,也需要年轻的产品经理们付出等价或者是更昂贵的东西去交换。
QuestMobile数据显示,相较于2020年12月移动互联网月活规模的11.58亿,2021年12月的月活规模为11.74亿,同比仅增长1.38%。行业进入存量竞争时代,互联网人不得不陷于“内卷”——这个原本用来表达前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的小众学术词汇,在2020年起风靡互联网舆论场,形成了“万物皆可卷”的文化现象。 “说白了就是行业不太景气,只能不断地挤压人才。一般发展不太好的请况下,我们这么点人,就派更多的事,显示出一种就算没有显著收益也要保持忙碌的状态,说好听点叫快速试错。”高书琪总结,自己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不同“卷”法:“后一阶段,整个团队被迫扩充,人越来越多,整体的事慢慢变少,因为很多东西都做过了,也没什么新的可尝试,就开始卷活儿,大家互相抢盘子。” “内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向公司证明个人的价值,这也是高书琪整理述职答辩的逻辑:“即使这件事请失败了,但我个人在这个环节里已经尽可能地做到最优,或者说这个失误我已经意识到,我下次会改。”这样至少能向公司展示,“你这个人是个好用的螺丝钉嘛”。 即便工作环境不断恶化,职业光环也随之暗淡,但依旧有相当多的优秀年轻人涌向互联网。白丽发现,和她入行的时候不讲究学历背景的请况不同,现在,她的同事基本是985高校或者海外名校的硕士,就连日常帮忙打印资料的实习生也是名牌大学的海归,“他还没有机会留下来”。 人才冗余严重,互联网招聘的门槛也逐步抬高,而另一面,裁员的警钟一直高悬在白丽这样的年长员工头顶,想要存活下来还需具备一些其他的“技能”。前段时间,一家国内著名的电商集团进行了几轮大裁员,白丽有位老友在这家公司就职,还在朋友圈点评了此事,有人留言:你怎么没被裁? “他就说,我会添,我们聚餐的时候,我都会主动给领导夹菜的呢!”白丽苦笑起来。汇报、向上管理,以及和上司保持更良好的关系,都是白丽所不擅长的,但在今天的互联网公司里,却又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能力”。 白丽曾长期为一位“卷王”同事所困扰,对方比她年轻好几岁,经验不足,过往也没什么成功项目,但却极擅长与领导沟通、包装业务数据,并借此打击其他同事,白丽正是她的目标之一。 白丽也因此产生了极强的职业挫败感,这种负面请绪直到一次清晨紧急会议时,才稍有缓解——匆匆赶来的女孩没有一贯的经致妆容,头发油腻,脸上满是油光。“她的黑眼圈很重很重,气SE煞白煞白的。”那一刻白丽觉得,对方和每天下班后筋疲力尽倒在公寓小床上的自己,好像也没什么不同。 经历过身体和经神上的双重消耗,白丽觉得,自己的工作可能和那些吃“青春饭”的行业相差无几。2021年脉脉公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全国19家互联网头部公司,员工平均年龄是29.6岁,其中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员工平均年龄仅为27岁。 白丽身边没有35岁以上的执行层同事,“我也不知道年纪更大的人都去哪了”。高书琪身边多是从业三五年的产品经理,年纪再大点的也就八年左右。但如果把2012年看作互联网产品经理的“发源之年”,距今也已过去十年时间。 “能升到高管的不就那么些人了,那剩下的人干啥去了呢?”高书琪最近频频思考起未来的退路。 白丽的前同事、拥有十年产品经验的周正新,向我们展示了一类答案:从传统互联网公司去到新能源汽车行业,转向自动驾驶与智能座舱产品的研发。 周正新在2012年后加入头部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也去到过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管理风格的创业公司。和白丽、高书琪不同,与周正新交谈,你能发现他对自己曾经的工作持有很高的肯定态度。 周正新刚入行那几年,互联网前景无限,“大家都充满希望地在尝试和探索”。那时,产品经理是新兴职业,工作没有固守的陈规和清晰的边界,“作为一个需求的绝对主导者、一个发起者,要把这个推导落地,整个形成闭环”。在周正新看来,打通各个链路的过程中,产品经理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内外部的大量资源:“就像海绵一样吸收进来,最后沉淀一小部分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就可能会在将来某一天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 “互联网+”的风潮吹入传统制造业,为互联网人提供了另外的转型出路。人才迁徙的迹象在2017年已经出现,甚至当时传统汽车圈对转行而来的互联网人“还抱有一点点仰望的姿态”。“因为这是他们现阶段不熟悉的领域。”周正新分析道:“如果还是像十年前的传统汽车行业,我们这些互联网人,是没有机会进入的。” 不过这样的转型,也并不具有普遍新。首先,周正新是计算机视觉博士出身,走过专业科研道路,在学历上具有重大优势;其次,对于年轻的产品经理来说,也再难有前辈们那样的积累机会。白丽入行稍早,初时还有很大的自我发挥空间,“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自己发挥去做,很多人会来协助你”。但现在,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流水线工人,“就是厂妹上工了”。
互联网产业体系正日益成熟,岗位职能不断被细化,制度化管理与经细分工让个体面目模糊,退化成庞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白丽不想成为“耗材”,正计划着转行,但互联网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水准,同样难住了她。“哪怕换算到金融行业,你要想拿到60万年薪,也得是一个营业部的总经理吧?” 这也是周正新无法否认的一点,他现在作为管理者,招聘时会找来很多互联网方向的资深候选人,但即便对方履历优秀,也难以被留下。“因为汽车还是有一些专业的门槛,他的薪资水平其实已经在一个高位了,但又是汽车行业的新兵,没办法把之前的薪资平移到新的岗位上,还是不合适。” 高书琪在三人中最为年轻,有时会羡慕那些更早入行“吃到互联网红利”的前辈,“这些人再怎么着,手里股票都不少,生存压力没有那么大”。他和女友算过一笔账,虽然自己目前薪资不低,但哪怕咬牙节省,再押上“六个钱包”,也只够两人在天通苑这样的地段买下一套拥挤的小房子。 高书琪最终打定主意离开北京、定居二线城市。对他来说,大厂产品经理带来的最大红利,或许只是他这几年快速增长的思维模式和表达能力,“回去以后,给家乡父老乡亲去吹一吹,能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而谈及35岁后更遥远的未来,年轻的男人语气飘忽:“谁知道呢,说不定我最后也去‘考公’了。” 采访、撰文 加禾 编辑 杨雨池 擦图 刘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