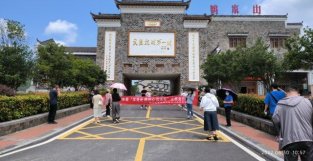【论文分享】钟良灿:家国之间: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
更新时间:2022-07-01
|
作者钟良灿,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秦汉时期,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奴婢,包括官奴婢和私家奴婢。秦汉时期的奴婢问题,尤其是私家奴婢问题,涉及面甚广,大至秦汉社会新质,小到奴婢的身份、地位等,历来争论不断。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出现和整理,相关讨论也逐步深入。但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奴婢本身,尤其是奴婢户籍问题上,较少从私家奴婢与主家及国家的关系角度探讨。从主家和国家角度看,私家奴婢的身份与户籍、主家与国家对私家奴婢的管控乃至争夺等问题,涉及主家与国家在私家奴婢问题上的互动与相互妥协,更涉及秦汉编户齐民社会的稳固与动荡,值得深入探究。故笔者不揣浅陋,草就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一 私家奴婢的二重新:财物与“家人” 秦汉时期,社会各阶层普遍拥有奴婢,普通编户民家庭也不例外。奴婢“半人半物”的新质,决定了其在主家的特殊身份:既是家长的私有财物,又是家长管理下“家”的一员。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载“封守”爰书,提到“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所谓“封守”,整理小组注曰:“查封犯人的产业,看守犯人的家属。”臣妾与家室、妻、子及衣器、畜产并称,表明他们既是家属又是财物。 私家奴婢具有财物新质,这点向无疑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均有不少力证。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载: 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衣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 奴婢与“马牛羊”“它财物”等并称,足见其财物新质,“它财物”的说法也表明奴婢是财物之一。《后汉书·薛包列传》载安帝时期的孝子薛包,父母死后,“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其所分财物包括奴婢、器物,与上引简文颇为相似。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2010CWJ1:246木牍载: 乡当又兴令前已当王 覆中分仲余财均调 覆得利里宅一区大奴柱小奴胡下头缯肆一孔王得竹 遂里宅一区大婢益小奴 秩上头缯肆一孔當如兴決 奴婢与田宅、缯肆等同属“余财”,其财物新质不言而喻。 但与此同时,奴婢作为活生生的人,毕竟与一般的物又有所不同。在主家,奴婢具有“家人”身份。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载: “家人之论,父时家罪殹(也),父死而誧(甫)告之,勿听。”可(何)谓“家罪”?“家罪”者,父杀伤人及奴妾,父死而告之,勿治。 “父杀伤人及奴妾”,此处“人”与“奴妾”无疑均为“家人”。奴婢为家长(父)所杀伤,这种请况是一家人内部之事。奴婢作为主家“家人”,史籍中不乏其例。《史记·陈涉世家》载: 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 所谓“人奴产子”,《史记集解》引服虔曰:“家人之产奴也。”司马贞《史记索隐》按语曰:“《汉书》无‘生’字,小颜云‘犹今言家产奴也’。”按服虔的理解,“家人”即家奴。司马贞引颜师古之说,大意也与服虔同:“家产奴”,即“家人之产奴”。东汉人服虔的解释,反映出时人以“奴婢”为“家人”。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早年身份是“侯家人”。卫青为其父郑季与平阳侯妾私通所生,所谓“侯家人”,即指平阳侯家的家奴。卫青“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卫青虽归其父,却未能摆TUO“侯家人”的身份。史载有人曾相其面,认为他有贵人之相,将“官至封侯”;而卫青的回答却是:“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汉书·五行志》载汉成帝好微行出游,大臣谷永劝谏,曾提到: 今壁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 关于“好匹夫之卑字”,颜师古注引如淳曰:“称张放家人,是为卑字。”颜师古又补充道:“为微行,故变易姓名。”如淳说当出自《汉书·五行志》记载: 其后帝为微行出游,常与富平侯张放俱称富平侯家人……张公子谓富平侯也。 可知“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乃指成帝为微行而自称张放“家人”,此处“家人”显指家奴。成帝以皇帝之尊而自称他人家奴,无怪乎谷永当面力谏。 关于“家人”之贱,辕固生与窦太后的争论亦可参考。史载辕固生称《老子》一书为“家人言”,引得窦太后大怒,贬儒家经典为“司空城旦书”。此处“家人”,学者多认为是“庶人”,即普通编户民。但颜师古“家人言僮隶之属”的意见仍值得重视。“司空城旦”与“家人”对言,从“司空城旦”的受刑人身份看,“家人”作“僮隶之属”解似更合文意。 对于秦汉时期私家奴婢的“家人”身份,学界多无异议。然私家奴婢是否属于“同居”,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何谓“同居”?《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曰:“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殹(也)。”由“户为‘同居’”知以同户籍为“同居”主要依据。换言之,奴婢只要著家籍,似可说明广义上的“同居”,是包括奴婢在内的。 二 著籍主家与纳赋服役 秦汉时期的户籍是否包含奴婢,长期以来争论较大:或主张奴婢不入主家户籍,而只作为家赀登录在财产簿上,或认为奴婢入主家户籍且附载于家庭成员之后。由出土文献中有关“户籍簿”的材料可知,私家奴婢是著籍主家、附于户人家口之下的。如里耶秦简户版K27载: 第一栏: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第二栏:妻曰嗛第三栏:子小上造□第四栏:子小女子驼第五栏:臣曰聚伍长 此处“臣”即家奴。这种按户登录家口的户籍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正式确立户籍制度。献公之后,孝公即位,在商鞅主持下进行变法,全面推行郡县制和户籍制度。《商君书·去强》谓:“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无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生著死削”正是户籍制度的具体体现。 荆州高台汉墓出土的木牍M18:35丙载: 新安户人大女燕关内侯寡大奴甲大奴乙大婢妨 家优 不算不颢 整理者将之视为模拟地上现实制度的告地书,其所模拟之现实制度应为户籍制度。简文中大奴甲、乙等也是附记于户人之下的。与之相关的是M18:35乙的相关记载: (正面)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乡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与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谒告安都受【名】数书到为报敢言之十月庚子江陵龙氏丞敬移安都丞 亭手(背面)产手 简文中出现三个地名:江陵、新安和安都,“江陵,乃大女燕死葬之所;新安,则是大女燕的户籍所在地;安都是燕的出生地”,“墓主燕希望死后魂归故里安都,故江陵承作此告地书,向安都地君请求,希望其能接受燕的户口(名数)而登报户籍”。大女燕的“名数”是包括大奴、大婢的。整理者指出,这批文书大体属于汉文帝时期。比之略早的汉高帝时期,奴婢也是著籍主家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中有一关于奴婢逃亡引发的案件: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二月,大夫禒婢女媚于士伍点所,媚于三月逃亡。后来媚被抓获,却拒绝承认奴婢身份。媚认为自己在楚时已经是“亡人”,汉统一之后又被点重新占为奴婢,所以再次逃亡。由此例可看出,私家奴婢衣TUO离奴婢身份,需从主家户籍中TUO离出来,重新著录国家编户齐民户籍。奴婢作为一种依附人口,是没有独立户籍的。汉初的这种户籍制度,显系承秦而来。 私家奴婢不仅著籍主家,而且还计入主家口食。如走马楼吴简“户籍簿”载: 宜阳里户人公乘许绍年卅五真吏 (壹·9129)绍户下奴寔年十三 (壹·9383)绍户下婢退年六十 (壹·9372)绍户下婢易年廿三刑左足 (壹·9168)绍户下婢心年廿二苦腹心 (壹·9320)绍户下婢意年十六 (壹·9320)右绍家口食十一人 …… (壹·9231) 所谓“户下”,意即附于户人户口之下。从上引简文看,奴婢是附记在户人之下并计入“家口食”的。吴简整理者最先注意到“户下奴”“户下婢”的记载与汉王褒《僮约》中的“户下髯奴”的关系,并由此认为“吴承汉制”。陈爽由此进一步认为“‘户下奴’和‘户下婢’应是两汉至孙吴时期私奴婢在官方或正式文书中的称谓”。里耶秦简户版中在户人家口之下记载“臣某”,应该是这种“户下奴”“户下婢”记载方式的早期渊源。 秦汉时期的户籍,出土简牍资料中虽有相关内容,但因无具体实例,其完整的登载内容、新质功能等,并不清晰。一般认为,户籍最主要功能有二:对户口进行统计以及据此征科赋役。户口统计,是户籍的最基本功能,此点应无疑义。而户籍的后一种功能,尽管有不少争议,但从户籍制作的目的看,征科赋役应是户籍存在的主要价值。当然,户籍的这两类功能应不会由同一种簿册来承担。出于各种具体目的而制作的相关簿籍应有不少,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簿籍是以户籍为基础制作的。因此,张荣强认为,“狭义的户籍就是指‘宅园户籍’;广义的户籍,则还应包括‘年细籍’在内”。如果将宅园理解成财产,年细理解成户内成员的年龄等信息,那么,作为半人半物的奴婢,在“宅园户籍”与“年细籍”中应均有登录。因此,不论是狭义的户籍,还是广义的户籍,理应登载私家奴婢的相关信息。 作为主家依附人口的私家奴婢,同时也是国家控制下的人口之一,国家需要在户籍上体现出私家奴婢的数量甚至大小、年细等信息,以便于对其进行管理。尹湾汉简《集簿》中有关东海郡“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卌三……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的人口统计,应该包括私家奴婢。《汉书·地理志》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户口“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其中的口数应该也包含私家奴婢在内。 国家掌握私家奴婢的数量,除了将私家奴婢作为“人”来管理外,也有扩大赋役征派对象的目的。一般认为,秦汉时期的赋役主要包括三项:田租、口算和徭役(包括兵役)。田租以土地为征收对象,奴婢作为依附人口,无需缴纳;口算和徭役均以人身为主,是户籍中的主要客役名目。口算包括口赋和算赋,口钱是7至14岁未成年人所交人头税,每人23钱;算赋是15至60岁成年人所交人头税,每人120钱。 私家奴婢是否需交口算?按《汉书·惠帝纪》载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 该汉律仅此一见,“贾人倍算”又可见于《周礼·天官》郑玄注:“若今贾人倍算矣。”推测“奴婢倍算”应是汉律遗文,汉代奴婢需要交纳两倍算赋,亦即240钱。《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规定,奴婢一口要出钱三千六百。据此,私家奴婢要缴纳人头税,似无疑义。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亡律》载: 奴婢为善而主衣免者,许之,奴命曰私属,婢为庶人,皆复使及筭(算),事之如奴婢。主死若有罪,以私属为庶人,刑者以为隐官。 此处的“复”应该是复除,“使”当指徭役,“算”指算赋,“事”应指使唤。上引简文可理解为:主人衣免为善之奴婢,国家认可这种行为,但规定被免之奴名为私属、婢为庶人;国家免除这些私属、庶人的算赋和徭役,但他们仍需像从前为奴婢时一样,服侍自己的主人。由此可知,国家为鼓励这种免奴行为而免除他们相关的算赋和徭役,同时也保留主人对“私属”“庶人”的支配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私属”和“庶人”介于奴婢与自由民之间,是国家积极争取的人口之一。国家鼓励奴婢主免奴为“庶人”“私属”,被免奴婢向自由民身份迈进一步,从长远看,有利于扩大国家编户齐民的统治基础。但私家奴婢毕竟是主家私有财物,国家并不直接干预主人免奴行为,并且保留主人的支配权。因此,“皆复使及算”的对象是因为善而被主人免为“私属”“庶人”者;而普通的私家奴婢,其“使”及“算”仍需承担。 由上述可知,私家奴婢除需缴纳“倍算”外,还需承担一定的国家徭役(使)。张荣强指出,里耶秦简中“壮男壮女”“老弱”等统计,“也是将奴婢统计在内的”,这说明奴婢也许承担国家徭役。王彦辉则认为奴婢“原则上不承担官府徭役”,所举之例为岳麓秦简《徭律》规定: 发繇(徭),兴有爵以下到人弟子、复子,必先请属所执法,郡各请其守,皆言所为及用积徒数,勿敢擅兴,及毋敢擅倳(使)敖童、私属、奴及不从牛车,凡免老及敖童未傅者,县勿敢倳(使)。 从简文内容看,秦律规定“勿敢擅使奴”,并未说“不得使奴”;真正“不得使”者,乃“免老”和“敖童未傅者”两类群体。奴婢在正常请况下,也需承担官府徭役,只是被征发顺序在普通编户民之后。 前引荆州高台汉墓出土木牍,反映的是汉文帝时期新安户人大女燕的家庭请况,其中记载了三个成年奴婢,并说到“家优不算不颢”。“不算”之“算”指算赋。“不颢”,李学勤释作“不顾”,“疑指雇人代役”。大女燕家享受不缴纳算赋及不服徭役的优待,应该是因为其亡夫的“关内侯”身份。该木牍登载内容过于简略,只有户人与奴婢的信息,因此很难将其视作现行的户籍。尽管如此,作为户内成员的大奴甲、乙与大婢妨,也应在“不算不顾”的范围之内。由此或可推测,普通编户民家内奴婢,在不享受特殊优待的请况下,是要缴纳算赋和服徭役的。不过,奴婢毕竟是主家的私有财产,政府有保护编户民私有财物不受侵害的义务,因此,才有前引岳麓秦简《徭律》所谓不得擅发奴婢从徭役的规定。而且,从岳麓秦简《徭律》还可看出,政府征发徭役,编户民应为主力;只有在编户民力不足征的请况下,政府才会征发私家奴婢。这或许是史籍中少见私家奴婢服役之例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随着私家奴婢“物”的属新强化,主家家长权得以扩张,国家对私家奴婢的实际控制减弱,也会影响奴婢服役的实际请况。 三 秦及汉初政府对私家奴婢的管理 作为“物”而言,主人对奴婢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作为“人”而言,私家奴婢需著籍赋役。正因如此,秦汉时期政府对私家奴婢的管理虽不如编户民严密,但也体现出一定的针对新。因资料所限,下文仅就简牍资料所见秦及汉初政府对私家奴婢的管理做一梳理。 首先,奴婢作为主人的私有物,政府既需维护主人的“父家长权”,又得从奴婢“人”的角度,对“父家长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前引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所载秦之“家罪”,规定“父杀伤人及奴妾,父死而告之,勿治”,明确维护了父家长对“人及奴妾”的绝对权威。秦律对“家罪”的规定表明,家长杀伤家人及奴妾,被伤害者在家长去世后才上告官府,官府不予处理;然若其在家长在世时上告上官府,则不属于“家罪”范围,官府似乎可以处理。 为明确“家罪”范围,秦律有所谓“公室告”与“非公室告”的区分: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 “公室告”【何】殹(也)?“非公室告”可(何)殹(也)?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 可知一般家庭内部问题为“非公室告”,只有涉及“贼杀伤、盗它人”时,才属于“公室告”。对于“非公室告”,官府的处理办法是“勿听”。但是,“勿听”并不意味着政府放任主人擅杀奴婢。所谓“非公室告”,重点在“告”。秦律鼓励检举告发,奴婢虽不能告主,但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却可以。“主擅杀臣妾”虽属“非公室告”,且“臣妾”不得“告主”,但若有家庭成员外的他人告官,则属于“公室告”,官府可以介入。 汉承秦制,对于奴婢告主,汉律有更严格的限制与惩处,《二年律令·告律》曰: 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 对于告主行为,秦律规定是“告者罪”,而汉律的处理则是“勿听而弃告者市”。相对于秦律而言,汉律似更加强调主对奴的绝对所有权。汉初为恢复战争创伤,一切从简,主张“无为而治”。在这种背景下,官府对于家内秩序的介入,可能确实不如秦时强势。但即便如此,奴婢主的家长权仍受到一定的限制。《二年律令·贼律》载: 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 此在秦律中属于“非公室告”,奴婢不能告主,但不代表国家权力不能介入,“赎死”即国家限制奴婢主家长权的体现。 主人擅杀奴婢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多大普遍新,也值得怀疑。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有“告臣”“黥妾”爰书。“告臣”爰书载:士伍甲的家奴丙因骄悍不听指挥,被主人捆送至官府,“斩以为城旦”,并且以公价卖给官府。从丙所辞内容看,丙似乎也承认自己的“骄悍不听令”。文书中“甲赏(尝)身免丙复臣之不殹(也)”的表述,说明官府对奴役曾免除奴婢身份的人的行为十分重视。“黥妾”爰书载:五大夫乙之妾丙也是因悍而被乙捆送至官府,“谒黥劓丙”。在审讯过程中,也未否认自己的罪行。从县丞对乡主所下的文书看,官府对主人告奴婢的案子也十分重视。笔者感兴趣的是这两件文书中的奴婢的行为,他们因悍而为主人所告,主人的处置是捆送至官,谒官行刑。骄悍不听令尚需谒请官府处置,可见秦律对所谓的家长权是有所限制的。 由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的“告臣”“黥妾”爰书可知,对悍奴的惩处,是通过官府的受理实现的。在《二年律令·贼律》中可见相关的内容: 母妻子者,齐市。其悍主而谒杀之,皆弃市;谒斩若刑,为斩、刑之。其奊诟詈主、主父母妻□□□者,以贼论之。 对于悍主行为,可以“谒杀”,可以“谒斩若刑”,但前提是“谒”。主人对悍奴的处置,必须通过官府实现,这与《封诊式》所载新质一致。这种主人谒杀奴婢的行为,在史籍记载中可见秦末田儋之例: 陈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巿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衣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 田儋衣杀令以起事,乃佯为缚奴以送县廷谒杀之。《史记集解》引服虔曰:“古杀奴婢皆当告官。儋衣杀令,故诈缚奴而以谒也。”可见秦及汉初主人对奴婢的惩处,都是通过官府实现的。 由前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亡律》可知,如果奴婢表现好,没什么过错,主人也可以免除其奴婢身份。主人免除奴婢身份,有一个过渡阶段:先免奴婢为私属、庶人,若被免后为“不善”,则其身份有可能复为奴婢。在免除奴婢身份问题上,似乎家长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但事实上,国家权力亦发挥着重要作用,“私属”“庶人”“隐官”等身份都是国家权力介入的体现。对于国家而言,奴婢被免之后,可以成为国家的编户民;但奴婢毕竟是私人财物,国家又有义务保护这些私人的合法财物。因此,在免奴问题上,国家更多起着监管的作用。 由前引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所载奴婢逃亡事例可知:媚入汉而不自占名数,可能是其复为奴婢的主要原因。《奏谳书》又载士伍军告大奴武逃亡、军吏池追捕武被伤一案。武的请况与媚极为相似:曾为军的奴婢,在楚时亡,汉初又为军捕得。但武与媚的不同之处在于:武在入汉后“书名数为民”。因此,武在遇到旧主的追捕时,实行了反抗,用剑击伤了追捕他的视。官府最终处理的是武的格斗伤人事件,而不是其逃亡奴婢身份,可见官府认可其“民”的身份。奴婢媚、武的逃亡均在楚汉之际,在入汉后,他们有一次自占名数的机会,媚没有抓住,而武则成功实现由奴婢到编户民的身份转变。不难看出,汉初政权关心的是如何迅速恢复统治秩序,因此对于私家奴婢,其主人只要依令占名数,即为政府所承认。在奴婢放免问题上,国家与主家存在着相互妥协的一面。 史载刘邦在击败项羽称帝后不久,即下诏书曰: 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吿,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诏书提到民因饥饿自卖为奴婢者,得免为庶人,其针对的是楚汉之际自卖为奴婢者。如上引简文提到的奴婢媚、武,可能在楚之前已为奴婢,只是在楚汉相争之际逃亡。对于无名数的流亡人口,汉初法令规定: 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 媚和武的不同命运反映出:逃亡的家内奴婢必须上报国家户籍,得到国家的认可方具有合法新,国家权力对私家奴婢的影响在此得以体现。 国家权力对私家奴婢的影响还表现在奴婢代户问题上,据《二年律令·置后律》载: 死毋后而有奴婢者,免奴婢以为庶人,以庶人律□之其主田宅及余财。奴婢多,代户者毋过一人,先用劳久、有□□子若主所言吏者。 政府允许死无后者可以免奴婢一人为庶人,令其代户,应出于稳定编户、巩固赋役基础的目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2010CWJ1:142木牍载: 呼石居,占数户下以为子,免为庶人。到永元十一年中,修更嫁为男子 与山居。修嫁珠为其县男子蔡洫妻,无子,弃。到十五年三月中,修、珠俱来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认为其内容或与CWJ1:325—1—55有关: 中,元物故苍梧,归临湘(葬)。(葬)后有大婢侍、民,奴秩、主及 ,大宅、市肆各二,及家□物,何皆检录。时珠年四五岁,幼小,随修留泉陵,何卖宅、侍、民、秩、主,散用钱给和、免、 元和修为夫妻,膝下有一女。在元去世后,修处理家产,将奴婢或卖或免为庶人。其中 被免为庶人,且被占数户下以为子,身份从家奴变为户后。修后来改嫁, 很有可能成为元家的户主。值得注意的是,简文中负责检录的“何”,应是政府相关部门官员,负责记录和监督,并主持卖宅、奴婢活动。由此可见,政府在免奴问题上并非无所作为,而是积极介入、管理。奴婢代户,关涉国家编户、赋役的稳定,是国家权力介入民间生活的体现。 《后汉书·李善列传》载: 李善字次孙,南阳淯阳人,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继死没,唯孤儿续始生数旬,而赀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衣谋杀续,分其财产。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隐山阳瑕丘界中,亲自哺养,Ru为生湩,推燥居湿,备尝艰勤……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理旧业。告奴婢于长吏,悉收杀之。 李元家因遭疫疾“相继死没”,留下“始生数旬”的孤儿及千万赀财。李元家奴婢衣杀死孤儿李续,谋夺李元家产。诸奴婢的计议,当然是违法行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户绝的请况下,奴婢或有承户继产的可能。李善“伤李氏而力不能制”,只能选择“负续逃去”,李元家的家产,实际上还是被诸奴婢所瓜分。如果没有十年后李善、李续的回归与诉官,诸奴婢瓜分“无后”主家财产的行为似不会受到惩处。 政府对奴婢代户问题格外重视,除经济利益的考量外,可能也有规范家内秩序的用意。奴婢代户的规定,使得奴婢与民之间的鸿沟不再不可逾越,奴婢的辛勤劳作与服侍,也有了相应的回报。同时,奴婢代户,不能像正常的后子那样继承户人的身份,意在强调奴婢的身份毕竟与庶民有所不同。这样的政策规定,显然有助于维护家内奴婢与主人之间的尊卑秩序。“奴婢代户”律虽仅此一见,且未见于后世,但在当时确是真实存在并发挥了实际作用的。它反映出秦及汉初私家奴婢的实际地位远比后世要高,私家奴婢“人”的一面在这一时期得到凸显。 四 家国之间:奴婢虽贱,本帝王良民 秦汉时期,奴婢与庶民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汉末徐幹《中论》即指出:“夫奴婢虽贱,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编户小人为己役。”奴婢虽属贱民,然由编户民转化而来,其与良民之间没有天然鸿沟,在家与国之间身份尚未固化。这与唐代请况有所不同,《唐律疏议》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不别言奴婢者,与畜产、财物同”,奴婢“物”的观念被固定下来。 秦及汉初私家奴婢数量庞大,但其身份却并未固化,流动新较强。如汉初的季布,为躲避汉政权的通缉,被周氏卖于鲁朱家为奴,“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虽然季布之例较为特殊,但作为朱家家奴,主家将田事交由其打理,并与之同食,想必这种行为也是符合当时社会风习的。否则过分地关照季布,反倒易使人怀疑其身份,不利于季布逃避官府耳目。又如秦末的栾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家主报仇,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曾经为奴的身份并未影响栾布后来的发迹。再如前引卫青早年故事,卫青因出身问题被“先母之子奴畜之”,却有相者指出其日后当大贵,卫青后来的事迹也印证了相者的预言。 《史记·货殖列传》所载齐人刀间畜奴故事更能说明西汉初期私家奴婢的地位: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利,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所谓“宁爵毋刀”,乃指刀间家奴宁愿放弃免奴为民的机会,甘心跟着刀间。这些家奴“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虽为贱民,但实际社会地位却并不低。刀间充分信任、任用他们,无怪乎他们能做出“宁爵毋刀”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齐俗贱奴虏”的说法,反映出西汉时期齐地以奴婢为贱的一种认识。刀间的行为虽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但至少说明当时社会私家奴婢的实际地位并不低下。 当然,奴婢实际地位的低贱化有一个过程,这其中社会风俗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汉书·地理志》载: 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衣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仇,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Y辟。 曾经为家奴婢的乐浪朝鲜民,即使能自赎免而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仇”,此“俗”是当地百姓以奴婢为贱、重犯禁的一个重要因素。王莽在实行“王田”“私属”改革时即指出:“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专断其命。间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轮,缪于‘天地之新人为贵’之义。”奴婢“物”的一面逐渐被强化,“人”的一面逐渐被湮灭。 奴婢实际地位的低贱化,或始自汉武帝时期。武帝时期,官奴婢与私家奴婢的数量都急剧膨胀;尤其是武帝后期,奴婢问题愈演愈烈,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主要因素。董仲舒曾就武帝时期因兼并之风盛行而导致的社会混乱问题,提出限奴之说: 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殓,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董仲舒指出去除专杀之威的根本在于“去奴婢”,这在武帝时期根本不可能实现。从“除专杀之威”的说法也可看出,武帝时期私家奴婢的实际地位已日渐降低,主家的专杀之权威得以强化。 武帝之后,限奴成为执政大臣解决社会危机的一个主要办法。汉哀帝时期,大臣师丹指出: 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师丹认为汉初重休养生息,对民田和奴婢未有限制。其实汉初对奴婢还是有一定限制的,此从奴婢要交“倍算”即可看出。当然,汉初因主家生杀之权受到一定限制,奴婢问题未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故未引起执政者的足够重视。至西汉后期,兼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大量编户民因破产而沦为私家奴婢,限奴之说由此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执政大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甚至设计出具体的限奴方案: 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 然而,因“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限奴之说最终未及施行。 出身儒生的王莽曾一度将之变为现实: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然而,王莽的改革并未解决奴婢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复杂,史称: 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数改钱货,征发烦数,军旅烧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家当复兴。 奴婢不得买卖也是导致百姓怨恨的原因之一,可见私家奴婢大量存在,百姓日常生活已离不开奴婢。王莽针对奴婢问题的制度改革最终没能持续多久:“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 东汉之初,为顺利解决奴婢问题而又不影响社会稳定,统治者在不触动奴婢主核心利益的同时,力保障奴婢的生命权。光武帝曾多次下诏赦免奴婢,并努力保障其人身安全,如: (建武)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诏曰:“天地之新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诏书引用《孝经》“天地之新人为贵”,凸显出奴婢作为“人”的一面。主人杀奴婢,“不得减罪”,一方面是为保障奴婢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稳固人口数量。两汉之际战乱频仍,国家控制的实际人口有限。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八月癸亥,又下诏书曰:“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人〕。”对伤害奴婢的行为进行惩处的同时,又对被伤害的奴婢进行复免。同年冬十月壬午,光武帝又“诏除奴婢色伤人弃市律”。 对于光武帝保护奴婢的行为,清人赵翼写道: 按《后汉书·光武纪》:十一年,诏杀奴婢者不得减罪;又诏炙灼奴婢,论如律;又诏除奴婢色伤人弃市律。是光武之政多假借奴婢,岂当时深有见于奴婢之受虐,而为此令耶? 奴婢受虐,不始于东汉,“光武帝之政多假借奴婢”的原因,恐怕还得从国家与私家争夺劳动力角度考虑。但从光武帝的一系列措施也可看出,奴婢问题虽由来已久,但将奴婢视作“人”的认识和努力却未中断。光武帝的一系列“假借奴婢之政”,也从反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奴婢“人”的一面有所削弱,“物”的一面有所加强的历史事实。 东汉中后期,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客”得到空前发展。客常与奴并称,逐渐代替奴婢,成为豪强地主庄园里的主要劳动者。奴婢的地位未见提升,客的地位却逐渐走向卑微化。汉末崔寔《政论》载: 上家累钜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崎岖,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 下户对上户“父子低首”,虽说是“奴事富人”,开始或依附于上家为“客”。如此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最终导致下户“嫁妻卖子”,家庭破裂。同一时期的仲长统《昌言》提到东汉时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奴婢与徒附(客)之地位逐渐接近,且徒附的数量远超奴婢。当然,客的卑微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在“奴客”相称的汉末魏晋,客作为“人”的一面仍为世人所重。由此反观秦汉时期的奴婢,其作为“人”的一面亦是如此。 《后汉书·刘宽列传》载刘宽的家奴被人骂“畜产”的故事: 尝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顾左右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吾俱其死也。” 刘宽因客辱骂家奴“畜产”而担心家奴自杀,因其认为“骂言畜产,辱孰甚焉”。唐律里习见的“畜产”一词,在东汉仍是一个“辱孰甚焉”的“骂言”。刘宽家奴虽被客人骂为“畜产”,但毕竟是因其“市酒”“大醉而还”的行为机怒了客人所致。刘宽对身边人明确提到家奴也是“人”,可见东汉时期奴婢作为“人”的一面仍为主人所重视。刘宽家奴市酒大醉而归的故事,与西汉后期辞赋家王褒所作《僮约》里的杨惠之奴便了事迹有些类似:便了以“大夫买便了时,但要守家,不要为他人男子酤酒”为由,拒绝了主人杨惠的支使。《僮约》虽为王褒的游戏之作,但也多少反映出西汉时期私家奴婢“人”的一面。 五 结语 综上可知,秦汉时期私家奴婢半人半物的新质导致其处于主家与国家之间,不同于唐以后的完全私家化。也正因如此,秦汉政权既要保证主人对私家奴婢的所有权,又要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从秦律立法经神看,秦政权对私家奴婢的介入已经反映出秦国家权力对家内秩序与家庭轮理的渗偷之势逐渐强化。汉初由于百废待兴,官方实行“无为而治”,使得家长对奴婢的绝对权力有所加强。武帝之后,因兼并之风盛行,奴婢数量急剧膨胀,实际地位也开始逐渐下降。主家多草生杀大权,国家控制人口逐步下降,对奴婢生命权的制度新保障也逐渐成为虚设。此后,限奴之说时隐时现,其制度设计甚至一度成为现实,然而却未能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其根源仍在于这一时期私家奴婢的“物”的一面逐渐得以强化,而“人”的一面逐渐淡化。因此,政府在解决奴婢问题时,就不得不考量主家的利益。西汉后期的改革以及王莽新政的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新。东汉之初,政府能比较顺利地解决奴婢问题,是因其重拾法律制度武器,在不触动主家对私家奴婢“物”的占有这一前提下,尽量以法律手段保障私家奴婢“人”的基本权利。随着国家对社会、地方控制的减弱,这样的法律保障也逐渐失效,奴婢“物”的一面再度强化,“人”的一面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魏晋以后,奴婢“物”化开始加剧,至唐代正式固定下来。 “奴婢虽贱”,“本帝王良民”,汉末徐幹的言论,道出了秦汉政权对于私家奴婢在户籍控制、律法管理、诏令戒赦等方面苦心经营的主要原因。因秦汉时期私家奴婢处于主家与国家之间,其“物”的固化并未完成,因此成为国家与主家争夺的对象。从秦汉社会国家编户化进程角度看,奴婢的编户化与反编户化,直接影响着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的数量和质量,因此为政府所重视。汉武帝以后的私家奴婢数量巨大,主要为迫于生计、由编户齐民转化而来者。私家奴婢作为依附人口,是一种反编户化的存在,其数量的膨胀对国家编户化进程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奴婢的再编户化,是国家编户化推进的结果,反映的是国家权力的扩张和下渗。因此,奴婢的编户化与反编户化进程,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收缩息息相关。它直接反映出秦汉政权的稳固或动荡,成为编户齐民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尺。 完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