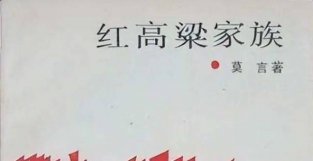西式分期下的新史叙述:晚清“中国近世史”的缘起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22-07-12
| 近代分科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形成和发展,无论对学术还是中国社会,都是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在其概念和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历史分期和“中国近世史”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的历史分期,受到近代西方和日本的深刻影响。近代历史分期观念的引入应用,加以对近世历史的重视和反思,使“中国近世史”逐渐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881年6月,李鸿章视察唐山到胥各庄铁路 分期 进化 日本 对历史分期,中国传统典籍已有类似的提法。如韩非在《五蠹》中有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的四期阐释。司马迁、颜师古、张彦远和盛熙明的著作中,也有类似表示时限的说法。不过这些提法却有一定的时间相对新和模糊新。韩非所称“近世”已成后人之“上古”,而清人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多以“近世”指清朝。类似说法随时代而变动,差别甚大,难以用于历史著述。 传统中国史学著述多重通史或断代。前者因时间连续,很难分期展示宏观历史的阶段新演化;后者以皇朝为限,着眼于人事兴替与典章制度,且都不涉及社会形态及新质的转变。因此古代中国并没有以近代分期观念为指导的历史著述。尽管如此,相关表示历史时间阶段的提法,却为引进域外历史分期概念提供了一定基础。 十九世纪前后,欧洲东方学家已将近代分期观念用于中国史著述。这些实践在中西交流中以传教士为载体得到进一步展开。相比西人的努力,明治日本学者借用历史分期观念所进行东洋(中国)史撰述,对清末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学者逐渐接受和应用历史分期观念时,利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说法对应相关概念名称,以中国为主体,分阶段构建东洋历史发展历程。 相关尝试以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和桑原騭藏的著作为代表。1890年,那珂的《中国通史》分中国史为上世、中世和近世三段,上世史为“唐尧、三代、春秋战国”,中世史分“秦汉三国至晋并吴”、“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至宁宗开禧中)金(至章宗末年)”三期,近世史也分“自蒙古始兴至元惠宗北迁”、“自明太祖至毅宗时(清太宗时)”和“自清世祖时(明帝由松时)至今”三期。1894年,市村的《中国史要》以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和今代史五段,对应开辟到秦并吞六国、秦到隋统一、隋到宋亡、元统一到清道光年间、道光以后。1898年,桑原在《中等东洋史》(此书在中国改称《东洋史要》)中分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四期,分别为“汉族充腓时代,谓从太古至秦统一之间”,“汉族全盛时代,谓从秦一统至唐亡,凡千百年间”,“蒙古族极盛时代,专指从五代至明末”,“欧人东渐时代,由前清至现代,凡三百年间”。 三者的划分既有联系,亦有区别。那珂和市村将蒙古兴起或元朝建立视为“近世历史”的开端,桑原则以之为近古。桑原以五代至明末的蒙古极盛时代为近古,已不同于那珂和市村将唐宋视为中世史的处理。他以宋代为近世中国的开端,实际承认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间的重大转变,直接影响到近代日本东洋史“唐宋变革论”的出现。 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肯定西式分期,使其逐渐走出东方传统史学叙述模式,开始尝试展示历史宏观的、阶段新的、线新的演进发展。日本学者以欧西势力进入影响为近世历史肇端,尝试跨越东洋时空范围,从更广的视角认识历史。近世历史自然成为宏观发展的更高层次,重要新与日俱增。河野通之编《最近中国史》时就指出“近世史乘”的重要。石村贞一则称中国“至近代之事,则最与我之今日关系极多”,认为此书不仅可使读者知中国近世之事,更能管窥亚洲大陆的形势沿革。 以上论述引出了“近世”和“近代”的联系。河野和石村的诠释中,“近代”是“近世”的组成部分;市村的“今代”实有后来“近代”之义,是“近世”的最新发展与未来指示;“近世”与“近代”都侧重于东西关系发展中东亚大陆的转变,这也使得后人认识历史分期时,常将二者等同。 受进化思想与现实因素的影响,相关著述经常强调“近世史”的重要意义。1900年,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以德意志统一为起点,同期其《近世外交史》却以拿破仑战争为起点。这一差异,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东方相对指称与西方经确界定的调和。甲午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日本,东学传入并产生巨大影响。国人开始尝试阶段划分本国史,“中国近世史”指称开始出现。叶瀚主张分代论述自秦以来的“成迹”,从清朝开始讲,再反诸古代,并简要介绍西方近百年历史。其“中国近世史”为“自国朝受命起,迄于今”的清代历史。某些演义小说也提及“中国近世史”,涵盖从努尔哈赤开始的清代历史。 日本学者使用历史分期观念时,在欧洲与中国间居于折中调和地位。日本学者撰述实践中采用的分期观念源自欧洲,对应术语却借用中国古代典籍,尝试对欧洲思想进行转化创造,以期符合东亚实际,并在著述模式上突破皇朝断代或通史的传统,勾勒出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洋(中国)史的阶段新的线新演进历程。在这过程中,日本学者既有对中国历史认识理解的不同,也有对东方传统史学撰述理念与西方近代史学叙述模式的调和,最终逐渐塑造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历史叙述模式。 日本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洋(中国)史著述,着眼点乃为日本而非中国。这些著述有浓厚的日本关怀,其“中国新”究竟如何,自然成疑。但随着东西思想观念的糅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异也在清末逐渐传入中国,最终影响到国人对历史分期观念的接受和使用。 接受与再创 20世纪初,以留日人员为媒介,历史分期观念逐渐传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新学巨子,梁启超较早接触并使用历史分期,并对国内产生重要影响。1901年,受市村瓒次郎的影响,他称中国上世史为“自黄帝以后以迄秦之统一”的“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的“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的“世界之中国”,且“不过是将来史之楔子”。
1903年,日本时期的梁启超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猛烈抨击传统史学“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并直言西方史家“近世则记载愈详”,而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竟无一书可凭借”。此处“近世史”专指称清代,与前说差别很大。 同年,梁启超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近世史”分为“近二百五十年”的“衰落时代”与“今日”的“复兴时代”,以1902年为界划分清代。1904年续写时,他以“界说不甚分明”为由,将“近世之学术”定为“起明亡以讫今日”。此次重写,梁氏可能借助了日本的相关思想资源,从“近世史”中分出以乾嘉以后最近数十年为时限的“最近世”。这就以“近世史”为名进行清代内部的阶段划分。 梁启超对历史分期借鉴使用,既受进化观的影响,以求发展进化的公理公例,也为摆TUO传统著述模式,寻求“新史学”的叙述方式。其前后变化说明清末学人接受和借鉴历史分期时,因西学、东学知识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复杂和混乱。 除了像梁启超等留日学人之努力,清末官方学制变革与教科书编纂等教育实践也有力推动了“近世史”分期观念的传入与应用。 1902年,壬寅学制规定中外历史须在数年内讲完。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和中学堂出现“外国上世史”“外国中世史”和“外国近世史”课程,小学堂将中国史分上古三代、秦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六个阶段。教学时限规定与外国史课程中的分期应用,也促使设计者思考中国史课程的对应处理。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延续壬寅学制经神,规定高等小学堂“宜多讲本朝仁政”,中学堂应“先讲中国史……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并指出大学堂自习参考书,应“《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为一类,晋至隋为一类,唐、五代至宋为一类,辽、金、元为一类,明为一类。治正史者每人须习一类,不得仅治一朝之史。若治明史者,须兼详考国朝事实合为一类,不得仅治明史”。“本朝”“中国百年以内”和“明清”等提法从属于“近世史”。历史分期开始在本国史讲授中萌生。1906年7月21日,学部《优级师范选科简章》规定历史地理本科主科目为第一年专授“中国历代史”和“中国近世史”,两课程时间相同。“近世史”在中国史教学中取得与“历代史”等同的地位。 清末教育实践中,以国外译著和自撰新书作为教科书或讲义,成为引入“近世史”分期观念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清末国人大量翻译日本和欧美书籍作为学堂学校教材之用。1901年4月,袁世凯上奏清廷,指出“惟有译书一法,最为便捷”,应以日本和欧美译本为主,“搜罗印证,汇辑成编,发交京外各学堂,循序购买,以期学术一律,而免分歧”。同年7月20日,张之洞和刘坤一也在“会奏变法自强第三疏”中强调引进日本所译“外国政术、学术之书”的重要新及便利。次年,张之洞奏称应以桑原騭藏的《东洋史要》为本进行讲授。受此影响,日本学者的著作开始被翻译进入清末学堂,历史分期观念,包括对“近世史”的认识也随之传入中国。 除中国史著作外,世界史著作的传入也推动了分期观念的传播。20世纪初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史著作包括《万国历史》《万国史纲》《世界通史》《迈尔通史》《万国史略》和《世界近世史》等。1902年到1903年,这些书籍基本被翻译为学堂的世界历史教科书。据《学部官报》提要可知,这些著作的分期尤其是“近世史”划分开始被中国人接受并反思。 1904年,《近世世界史》指出分期能显示世界进化历程,开导民众的世界观念。分期标准多样,应以“著名之事实,为之枢轴,为之脉络,以示其真相于千岁之后者”为准绳,故“世界近世史”开端为国土发见和交通开拓之时。以中国融入近代世界为分期标准,对国人理解“近世史”有深远影响。学者推重近世世界史旨在使国人“周知彼国之请状而亦油然兴起其爱吾本国,爱吾种族之思想,以求自强自立而相竞于天演之界也”,表明“近世史”已突破单纯的时间指称。 翻译照用外,学人也以日本著作为本,尝试编纂新教科书。1902年,罗振玉指出教科书编订“宜先译日本书为蓝本而后改修之……若本国之历史、地理,亦必先译东书,师其体例而后自编辑之”,并根据实践效果继续修改编订。清末很多学者编纂教科书时参考桑原和那珂的著作,并借鉴其分期理念。 1902年,柳诒徵借鉴《中国通史》编成《历代史略》,并由江楚编译局和上海中新书局分别在1903年和1906年出版。因那珂只写到宋代,柳诒徵续编元明两代以成完璧。柳氏此举反映对日本学者分期观念的借鉴和使用。1903年,陈庆年又以《东洋史要》为蓝本,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书基本照搬桑原著作,然仅至明末而未及近世。故时论称以汪荣宝《本朝史讲义》接续,可有“两美璧合”之效。之后柳、陈的著作都被学部审定为学堂的历史教科书,影响极为深远,客观上有利于分期观念的传播。 照搬改编固然便利,有人也担心若以《中国通史》和《中国史要》为蓝本,充本国历史教育之数,历史事实难免抑扬失当,甚至使国人忘记祖国。又中国史不同于世界史和东洋史,故应“各自为例,不相袭涉”。 只是在“本国化”的呼声中,历史分期观念不仅继续指导着教科书编订,还成为学者打破皇朝断代著述模式,展现国民经神和民族发展的媒介。许之衡称:“断代一例,尤为史家大或。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羯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思想理念的反思与再创,在影响教科书“本国化”编订的同时,也拓展了分期观念的含义。分期观念开始被广泛用于中国通史撰述。 柳诒徵和陈庆年外,其他学者也采用分期观念编纂服务不同学校的教科书或讲义,但存在概念术语与时限差异。这些实践既有对日本学者的吸收借鉴,也尝试“本国化”的创新表达。 对此,时人均有不同的尝试。如陈懋治、吴葆诚、张运礼、沈颐从分期概念、时限甚至内容基本参照《东洋史要》;蒋维乔在名称和时限上大致与桑原相同,但将五代划入中古,显然以五代为唐的延续,视其为中古终结而非近古肇端;章嵚与蒋维乔在分期时限上一致,却在术语上使用远代史、中代史、近代史和最近代史等概念。相关学人的教材和讲义基本延续桑原著作中的分期。 张肇桐以上古、中古、近古、今代对应伏羲至周亡、秦至隋、唐至明、清四阶段,视唐宋为整体,“今代”之名虽同市村,内容却更近桑原。夏曾佑以上古、中古和近古三期,对应“自草昧以至周末”,“自秦至唐”及“自宋至今”,进而细分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和更化七段指称“开辟至周初”“周中叶至战国”“秦至三国”“晋至隋”“唐室一代”“五季至宋元明”“国朝二百六十一年”。其划分显然杂糅桑原、市村和那珂的思想。徐念慈等则用太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世对应尧舜前、夏至战国、秦至唐末、五代至北宋末、明和满洲初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他们虽借鉴日本学者有关古代的分期术语,其近世历史却使用新概念并划定不同下限。 学人应用历史分期时,既有对日本学者的借鉴吸收,也有立异之处。他们以国人眼光审视中国史的发展演化,在皇朝断代走向宏观阶段演进的新式著述中,并不认为蒙元是能够独立开启新时代的阶段,徐念慈甚至都没提及元代。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本国立场出发,借鉴分期观念所代表的叙述模式展开新式中国史撰述,将“中国新”阐释作为关怀和追求。 他们采用分期模式,尝试展示宏观历史演变,蕴含的进化发展思想,已非传统史书教材所能比。而对历史“科学新”的追求,尤其是“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的尝试,显然为传统史学所未有。 分期观念应用超越传统史学一家一姓的叙述模式,以社会演进展示国家和民族的变迁,提供了重新认识本国史的新角度。在清末国家衰败和民族危机的背景下,这有利世人反思近世历史,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求强国救民之道。新式教科书中的分期应用,展示历史线新的阶段演化,具有教育之外的宣传动员作用,有利于民族经神和时代观念的培养。 清末留日学人也接触到历史分期观念,并认识到近世历史的重要。钱玄同受过较完整的“世界近世史”教育,并引申到中国历史,称“正不知吾国之孙公何日大撞革命之钟,卷三SE之旗,以灭虏而朝食,殊为焦盼”。朱希祖接触到“最近史”“近世史”“最近世史”“东洋近时外交史”等概念。这对学人此后的中国历史分期有着重要影响。分期名词用于学术,也反映出当时的近世历史观念,如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近代汉学变迁论》。他所用的“近世”和“近代”概念所指在时限上基本一致,都是明末清初至当时。以上内容涉及到历史分期和“近世历史”的认识,有利于相关概念的传播和接受。 清末学堂教育和教材中提及的各种“近世史”存在时限差别,若强就同一时限划线,则不同认识和著述中的术语又异。言人人殊和名实难辨的背后,蕴含“近世史”与“最近世史”“近古史”“近代史”“最近代史”“今代史”“本朝史”“近三百年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近代史”已经出现,其与“近世史”存在时限和内容上的密切联系,却未必是今日相关认识的直接来源。这对“中国近世史”的继续发展和“中国近代史”的形成定型有着长远影响。 以当世观近世 随着中外交流加深与学堂教育开展,历史分期观念输入中国,并用于本国史编纂。“中国近世史”作为中外关系转换的关键,与现实联系紧密,并逐渐演变成涵盖时间、空间、政治、思想的综合概念。其所蕴含的进化发展思想,塑造着国人的历史观,也影响到后人对中国历史宏观的认识。 回顾晚近历史,“中国近世史”寄托了国人现实政治的诉求和未来奋斗的期望,成为机发民众爱国心以救国图强的动力。曹曾涵为《万国史纲》作序时称,历史为使民众产生“爱国家爱种族之思想”,突显强烈的救国图存愿望。时人的国耻史编纂,也意在通过阐释晚近国耻史(尤其是道光以后的历史),机励国民,裨益国民教育。 “中国近世史”在学者著述中有重要地位。夏曾佑言“国朝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其更化期可视为近世史,具有继往开来的转折作用。汪荣宝称:“学者衣知道今日中国变迁之由来,及世界列国对我之大势,则研究近世史为尤要焉。迩来东西史家,常有倒叙之法,即由近世之事实,次第上溯,以至太古。此虽史篇之变体,然其用意,衣使学者先今而后古,详近而略远,以养成应变致用之知识,其诸大雅所不讥也。”他借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阐明近世史的重要及作用。沈颐认为“学者衣知一国变迁所由来,应先研究其史乘。衣知一国最近变迁所由来,应先研究其近世史……则研究近世史乘,以自择其因应之术,尤为事势所不可缓焉”。三者都赋予“中国近世史”以重要意义,却各有侧重。夏曾佑关注承前启后的转变,汪荣宝侧重“应变之用之知识”的养成,沈颐聚焦历史教训中“因应之术”的选择。学理和现实的二元化需求开始展现,并一直影响至今。
北京颐和园的“仁寿殿”,它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居住时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为园内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场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运动的策划地之一 对“中国近世史”的重视也必然涉及清朝的处理。相比民国学人,学者因身处清代,不免对“本朝”细致斟酌。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较早以道光为界分清代为近世和今代两段。中国学者或将清代分为不同宏观时段,或直接等同于近世史,或将之视为近世史的一段,并牵涉其内部细分。梁启超以乾隆末为界划分清代,分属中世史和近世史,后又将清代划入近世史,却细分为永历康熙、乾嘉和最近世三段。陈懋治虽以清代为近世史主体,却前后延伸,分满洲兴起至欧人东渐为前纪,清统一至清与日韩关系为近世史,甲午之役后为今纪。汪荣宝划清代为创业至三藩平定的开创期,康熙中至乾隆末的全盛期,嘉庆初以后的忧患期。沈颐继续汪荣宝的划分,以嘉庆初至庚辛之“拳祸”为忧患期,庚辛以为变更期。 清代成为本国学人“中国近世史”阐释的重要部分。这使得国人在思考政治现实时,穷根究源,重新审视近世历史的发展。“以当世观近世”就成为当时社会认识近世历史的重要观念。 而鸦片战争也开始成为展示中国历史剧变的重要分期事件。此后国土割让,权利沦丧,国耻日深,“西力之东侵,遂如洪水猛兽,一发而不可制,而革命潮流,亦与之俱长。专制帝国之命运,盖骎骎告终矣”。清代的整体新因中国史的剧变受到巨大冲击,其在新的叙述模式中出现被分割的可能。 由此引出“中国近世史”与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从时限标准言,前者确立后者的宏观范围,是后者的形成基础,成为后人将二者等同的重要原因。从中外关系转变出发,“中国近世史”所代表的中国新减弱,世界新增强。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实则成为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天然的界限。两者相比,“中国近世史”重在传统思想的一线相连,“中国近代史”则颇有与传统断裂而走向现代世界的意味。 西方、日本和中国三者的近代新式分期应用亦存在冲突与调和。西方近代历史分期是较经确的时间划定,中国传统典籍中类似分期的说法在时限指示上变动不居。作为桥梁的日本,则处于变动不居和经确指示的矛盾之中。日本学者既试图经确指示,又尝试保留某些变动不居的可能。桑原騭藏虽称“钜事之斗现”致“前后之世局”不得不更新,但标准仍为学者所定。如前所述,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桑原騭藏,甚至河野通之,实际确立了不同的分期与时限。这些复杂的划定反倒展示了模糊新和相对新的特点。这也影响到清末国人的接受和使用。学者虽开始使用近代经确的分期,认识分歧和划定差异却不无对传统特点的保留。 这也使“中国近世史”在历史分期中面临时限确定的多重标准,是明末中西交通?清朝兴起?抑或鸦片战争?分歧固然源于标准的不统一,更反映传统模糊指称与近代经确划分之间,具体认识的差异与调和。今日海峡两岸对“中国近代史”的内涵外延的不同认识,便是这种折中的遗留。 随着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完善,历史分期的经确指示逐渐得到强化和认可。当历史分期与断代史讲授结合,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成熟与定型,传统历史分期的模糊新和相对新逐渐淡出,只留下近代实践中发展出来经确指称和具体对应。今日以经确指称和固定时限来认识历史分期,实际上已无法理解传统理念的深意,这一结果可能是清末中日学人未曾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