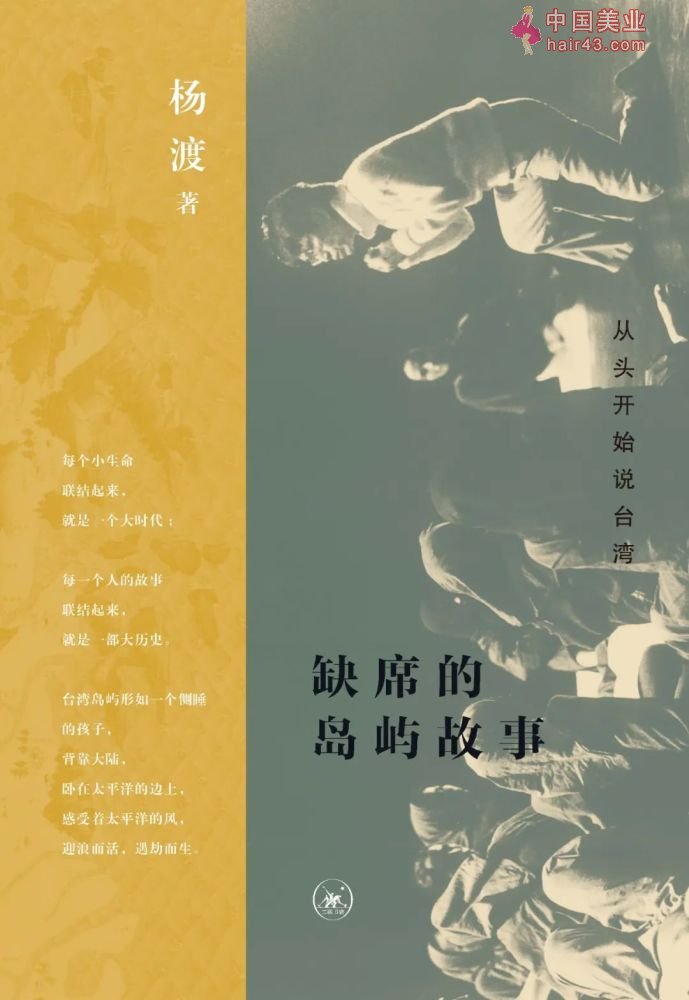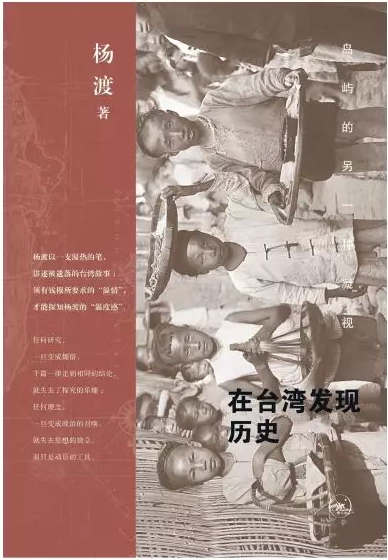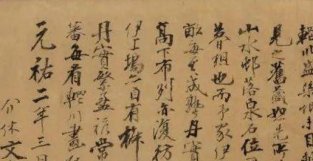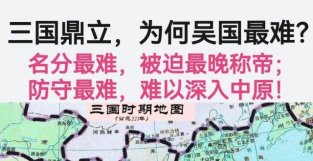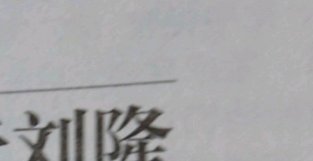台湾光复,巨变瞬间的人间容颜
更新时间:2022-08-04
| 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 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十月二十五日,台北公会堂坐满了台湾各界的代表。十时整,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率领谏山春树参谋等人,身着军服,走入会场,向受降官敬礼。陈仪受礼完毕,即席宣读受降书。安藤利吉在降书上签字,完成仪式,立即退席。日本殖民统治,也从这一刻起,随着安藤利吉从台湾退席。 陈仪在台上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的版图。” *文章节选自《缺席的岛屿故事:从头开始说台湾》(杨渡 著 三联书店2022-1)。
庆祝台湾光复——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典礼 台湾光复的那一刹那 小学六年级的那一年,林文月在上海就读日侨小学。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中午,学校召集老师和学生,要一起听“天皇玉音放送”。“玉音放送”是重大的事,学校召集师生在礼堂里安静地听着。天皇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的“无条件投降”的声音,像一面大鼓击打着师生的心。刚开始大家眼神茫然悲哀地相望,随后整个礼堂里,充满哭泣的声音,久久无法平息。 林文月回到家中,发现家人庆幸着:战争终于结束了,台湾结束殖民统治。家人告诉她,我们现在属于战胜国的一方,不再是被殖民统治的二等公民。新的时代来临了。然而过了几天,上海的街道起了变化,日本人要被遣送回国,但作为战胜国子民的台湾人却没有人管。街上开始抓“汉间”。举凡穿着日式和服或者与日本有往来的人,都被视为汉间,在路上会被抓、被打。经过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人的生活基本已经日本化,一下子要改变也很难。何况他们住在租借区,非常危险。林文月的母亲是连雅堂的长女,连雅堂是写《台湾通史》的文化人,他们并无政治上的依靠。不得已,全家赶紧搬回台湾。那一年秋天,她回到台北开始上小学,学习中文。 林文月是一个典型。 对台湾人来说,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不是像香港,有一个租借的时限,而是无限期被割让出去,没有人知道是五十年还是一百年。五十年后依照《开罗宣言》而来的“重回祖国怀抱”,竟像一场梦。人们起初都不敢相信。 *** 八月十五日那一天,陈逸松在律师事务所习惯新地打开收音机。前一天他已经听说次日有“重大放送”,所以特地抽空听一下。但他的收音机新能有些问题,杂音很重,听不清楚,只隐约听到“一心一意”“奋战”等字眼,他心想,还不是鼓吹“圣战”而已,于是走到隔壁的山水亭去找音乐家王井泉吃饭聊天。 两人正在闲聊的时候,曾强B陈逸松“无罪自首”好让自己升官的台北州特高警部补佐佐木仓皇地跑上楼来,一脸惊惶地问道:“陈先生,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想?”陈逸松吃过他的苦头,怕是在套话,以罗织罪名,就不痛不痒回道:“只有照天皇陛下所宣示继续奋战而已。” “唉!我听是日本战败宣布投降,怎么会继续作战呢?是不是我听错了?请你们两位稍候,我先回去州厅再仔细打听,马上就回来。” 佐佐木飞也似的冲下楼去,留下两个老朋友面面相觑,王井泉的脸颊微微颤抖着,望着陈逸松说:“佐佐木不像是在开玩笑,你是不是听错了?日本真的投降了?” “佐佐木说的恐怕是真的,我那破收音机根本听不清楚。”陈逸松记得,大约有十分钟的光景,他们两个人沉默不语,多少年的心事、多少年的奋斗、多少年的梦想,竟然有这一天。王井泉轻声说:“日本若输去,我们所期盼的较理想的社会就会实现了。大家要好好努力呀!” 过不久,佐佐木回来了。他机动地说:“陈先生,王先生,日本输去了。日本输去了。太久受大家招呼,真感谢你们!”说完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下楼走了。 王井泉去厨房沏了一壶好茶,两人静静相对,面含微笑,慢慢品尝。陈逸松永远记得那个茶香,因为几十年来,他未曾如此轻松过,此生第一次,放心、安心、静心闻到茶香。 *** 陈逸松的作家好友,台南医生吴新荣在那一天中午打开收音机,要听天皇广播,发现它没电,就作罢了。晚上,他的好朋友跑来找他,慌慌张张地告诉他天皇播放的内容。他吓了一大跳。但也不敢真的相信。长久的压制让他保持警惕。他年轻时候坐过牢,这让他学会不要相信殖民统治者。次日上午,吴新荣照常去诊所出诊后,才约了几个朋友来到郊外,把衣服都TUO了,跳到溪水中,他们要“洗落十年来的战尘,及五十年来的苦汗”。上岸后,在空旷的天地间,在无外人的海边,吴新荣放心地对着大海高喊:“今日起,要开始我们的新生命啦!” 第三天清早,他到一个防空壕里拿出一座祖先的神位,把日本强制摆放的“神棚”移开,斋戒沐浴后,焚香向祖先在天之灵祭拜说:日本已经投降,祖国得到最后的胜利,台湾将要光复!但此时的吴新荣并不放心,台湾民众尽管也在街道上张灯结彩,但内心还有隐忧。因为日本还有近十七万军人,加上日本居民,合计有五十几万。他们是要去要留,还未决定;如果留下,会不会发生变量?他们会不会大开杀戒?未来中国将如何接收?国际局势会如何演变?这谁也不敢说啊! 吴新荣为了探听消息,特地应一个日本朋友的邀约,去他的家里探望。那日本朋友姓平柳,主管特务工作,因为长期监视吴新荣而有交集。他把吴新荣请到了他的防空壕里。在战争后期,美军时常轰炸的时代,许多台湾人都躲到乡下疏散,日本特务无法疏散,做一个大防空壕并不意外。只是吴新荣没想到这个防空壕点着灯,不仅灯光明亮,还备有美酒佳肴。 “日本到底战败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变成战败国民。”平柳丧气地说。 “但台湾人也不是赢了,怎能说是胜利国民呢?因为我们一向是顺从的,在这连战连败的中间,也未曾和你们抵抗过。” 事实上,到了战争后期,军国主义横行,所有反抗都已被压制,连用收音机听大陆的广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中央书局的庄垂胜就是因此坐了一年的牢,严酷至此,谁敢反抗呢? “是,是,这我们也知道,所以未曾放行那个最后处置。”平柳说。 “什么最后处置?” “这也是过去的问题了,所以我也愿意说给你听。最后的处置是日本军部的政策,于各街庄(镇、乡)将庙宇改成一个临时的收容所,至最后阶段,将所有的指导分子监禁起来。” “什么是指导分子?” “像街庄长、大地主、地方有力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黑名单人物。” “这地方的黑名单人物是谁?” “第一名是吴三连,第二名是庄真(庄垂胜),第三名就是你了。但是这份黑名单昨日已经烧掉了。” “可是这为什么要烧掉呢?这不是国民党政府的功臣榜?”虽然这样轻松地说着,吴新荣却被吓出一身冷汗。 他曾听台北的朋友说,日本特务手上有一份黑名单,若美军攻台,就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杀了,以避免和美军里应外合。幸好最后没有发生,否则自己命丧何处都不知道,更可怕的是,这简直是对台湾经英的大屠杀。 他定了定神,问道:“你想日本将来要向哪里去?” “日本人最听天皇的话,所以这次的投降,以天皇的命令一定不发生问题。但是日本已经属无产国家了,即使有一句‘天皇共产制’的话,我想这也许最适合日本的现况,我归国后也向这条路走。”平柳说。 吴新荣要得到的答案已经有了。他其实最想知道的是,在台湾的日本人会不会不甘心战败,最后负隅顽抗。显然,日本人“最听天皇的话”,应该就是放弃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准备回日本。至于日本未来如何走,已经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了。他更关心的是:台湾未来要如何重新开始。 *** 吴新荣的忧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最不甘心离开台湾的,是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日本政府官僚,特别是长期居留,已经习惯了台湾生活的日本人。 他们在台湾有特权、有房子、有财产,有各种优渥的生活条件、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有各种人脉关系。一旦离开,财产全部归零,回到日本,他们将一无所有,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 台湾人之中也有殖民统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如辜显荣家(辜显荣已过世,由辜振甫主持家族事业)以及一些御用绅士如许丙、板桥林家的林熊祥等,他们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于是和日本军部的少壮派军人结合起来,计划号召更多士绅组成“台湾政府”。日本少壮派军人认为台湾有十七万军人,还有五十几万日本人,结合台湾地方士绅地主,未必没有机会一搏。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草山会议”。在计划中,他们打算请雾峰林家的林献堂担任“独立政府”的委员长,板桥林家的林熊祥担任副委员长,辜振甫任总务长,许丙为顾问。 汹涌的暗潮不只是“独立运动”。 八月二十二日左右,一个叫秋水大尉的日本军官来到陈逸松事务所,直接表明:台湾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许多日本人来到台湾,现在有近五十万居民,他们都很爱台湾,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故乡,而今日本战败,能否向中国政府租借台湾,租期五十年,租金每年三百万元。陈逸松当场拒绝。那日本军官不死心,继续说:“可是我们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台湾,要是台湾人同意,我们再在国际上办交涉。”陈逸松拒绝道:“这个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怎么去说?” 无论“独立运动”与“租借”,都可以反映出在这无政府的时刻,在政权更换的巨变下,台湾是如何的不稳定。 但是在民间,日本的中下层公务员、教师等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他们带不走的东西,如家具、钢琴、书籍等,都以便宜价格出售。厦门街一带是日本公务员居住的地方,他们把东西摆在街道边出售,慢慢形成了市集,后来这里竟成为旧书与旧货的市场。至今,厦门街仍是旧家具的卖场,旁边的牯岭街一度是台湾最大的旧书市集,后来虽然迁到光华商场,但还是有几家老店不走。如今书市不景气,但二手书并未没落,牯岭街依然有不少家旧书店。这都是一九四五年巨变遗留的风貌。
一九四八年,中研院第一届院士中,百分之二十五来台,百分之七十五留在大陆 巨变瞬间的人间容颜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台湾新报》在八月八日有一则新闻登在重要的版面上: “敌人以暴虐无道的手段,轰炸中小城市,造成平民、妇人甚至孩童的大量死亡……这是非人间的杀人行为。”报纸公布的死亡统计,有九百六十四名,其中男新四百四十人,女新五百二十四人,而十二岁以下孩童有二百三十四人。 这是广岛原子弹轰炸的报道。 台湾人从可以读到的有限消息里,早已看出胜负,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军方强征民间铜铁物资,甚至连中学生也被强征入伍,就已败象俱现。 一九四五年二月,台南人林书扬(台湾被关押最久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治犯,在狱中长达三十四年)还未到年龄就被征召入伍。部队中大多是嘉南一带的农村青年,他们在晚上熄灯后,偷偷来找林书扬,请他教英语,只要一句:“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这些青年认为,美军攻陷菲律宾之后,就会攻打台湾,如果美军登陆时被捕,说出这一句或许有用吧。 在美军的轰炸之下,许多人都疏散到乡下,以躲避战火。谢雪红在被关了十二年之后,回到台中市,疏散到台中山区的头汴坑,靠几分地过活,食物不够,只能种番薯过日子,鱼肉完全断绝,要买白米得去黑市,他们买不起。原台共党员苏新则在出狱后,回到台南,靠养兔子过活。此时食物全面管制,不能私自屠猪宰机,家畜得上交给当局,才能得到一点补偿新的肉食。为了有助于农民应对困境,苏新还写了一本教农民如何养兔子的书,至少兔子是不必上交的。简吉则是回到凤山,因为他的活动能量太强,在农民之中影响力太大,干脆被看管起来。 日本宣布投降时,林书扬还记得“那一刻胸中的沸腾,解放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欢欣期待,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在嘉义的街头,开始出现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各种中文歌曲的知识分子。老一辈的汉语老师被重新找出来,教大家学习中文。“皇民化”政策之后,中文教学被全面禁止,只能悄悄教,现在终于可以公开了。受了五十年日本教育的台湾人,一夕之间回到自己父祖的文化中,许多人像吴新荣那样,把祖先的牌位摆出来,取代那被强迫摆上去的日本神道,用古老的仪式,焚香告祭祖先:台湾光复了。 谢雪红回到台中市,她联络朋友,希望日据时期被停止的社会运动团体可以重建,并开始找人筹组“人民协会”。台北的陈逸松找出一盘以前从大陆偷偷带回来的唱片,在文化人王井泉家的山水亭播放。现场一起听的还有吕泉生。吕泉生是台湾第一个采集民谣的乡土音乐家。一九四三年,“厚生演剧”在永乐座公演《阉机》的时候,他用两首台湾民谣的合唱曲《六月田水》和《丢丢铜仔》,感动了观众,轰动一时。没想到日本警察受不了,第二天就加以取缔禁唱。 吕泉生在山水亭听到这些歌,就在现场用五线谱记下曲谱,并写下歌词,再借了钢板、铁笔和蜡纸,印出来分发给民众。他还高兴地到街头去教唱。 *** 但怎么往下走?中国与美军没有消息,大家都没有底。好不容易过了半个月之后,终于有消息了。第一批到台湾的官员是跟着美军飞机来到的。那是九月二日,来的有国民党政府官员三人:第一个是福建省政府顾问黄澄渊,第二个是中美合作所的黄昭明;第三个是“台湾义勇队”的副队长张士德。他们住进台北最豪华的宾馆──梅屋敷。 九月三日,与“总督”的会谈在台北宾馆举行,张士德将带回来的第一面国旗,擦在台北宾馆里,正式宣告日据时期结束,中国政府来了。 随后,张士德开始拜会台北重要的地方领袖。他以“台湾义勇队”副队长的名义联络陈逸松。刚一见面,张士德就用闽南话直截了当地说:“国军很快就会来了,但国军来之前,为了防止日本人可能有的破坏行为,希望你能出面组织台湾的青年人,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保护国家财产的安全。” 陈逸松义无反顾地同意了。张士德当场拿出一张红纸,写上“日日命令”,内容是:“任命陈逸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主任。” 陈逸松是学法律出身的,没看过法律上有这个“日日命令”的用语,不知道在大陆是什么意思。张士德解释说:“这就跟行军一样,现场可以发布命令,等于军令。” 陈逸松陪着张士德到访好几个地方:台北、淡水、三芝、宜兰、罗东、新竹、台中。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舞龙舞狮、锣鼓鞭炮、夹道欢呼,比迎妈祖还热闹。有的地方还特别杀猪欢宴宾客,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庆祝光复,对祖国来的第一个代表(特别他又是一个台湾人)表示热诚的欢迎。张士德成为“台湾真正光复”的象征。 在“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主任”的名义下,陈逸松急于把台湾各界的经英组织起来。他找了过去抗日的知识分子、农民组合干部、文化协会成员、“台湾民众党”干部等。虽然大家对大陆的政治请况、政府体系、派系分布、人脉关系等,完全不了解,甚至连“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的定位都不清楚,但在“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这个堂皇的名号下,怀着战后对台湾的建设、对祖国的建设有所奉献的希望,参与到“三青团”的工作上来。 日本人的“御用绅士”是一定不能用的。他们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作威作福,享受荣华富贵,但这些见风转舵的投机分子,如今却都毫不犹豫地到处花钱拉关系,改投到“三青团”的名下,想要挤进来弄一个职位。为了快速建立起各地组织,陈逸松没办法一一查证,他只能把组织工作交给各地主要负责人来做,相信他们最清楚谁是真正的抗日志士,谁是“御用绅士”。他自兼青年团台北分团的团长;新竹是陈旺成,台中为张信义、杨贵(即作家杨逵),嘉义是刘传来,台南吴新荣、庄孟侯,高雄是杨金虎、简吉等。组织的规章由台北制订,运作上则交由各地自行负责。 然而,复杂的请势很快在各地发生。吴新荣在台南就明显感到“御用绅士”的威力,他们试图加入“三青团”未果,就组织各种“欢迎政府筹备会”“治安维持会”等,并请他担任副委员长。他虽然拒绝,但他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对方筹组团体,只能是各走各的路。也正因此,埋下了这些“御用绅士”后来在“二二八事件”中告密陷害吴新荣的祸根。 九月十九日,《台湾新报》发布了陈仪将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之后,主权交接落到了实处,于是过去被殖民统治者欺负侮辱过的人开始了报复。先是围殴追打日本警察的“走狗”,之后是打日本警察,再后来,素有仇隙的人之间也互相报复起来。 社会也已经悄悄地开始发生变化。有喜悦有活力,民间有勃勃生气,但也有隐隐偷出的犯罪与不安。 看一下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 一到了夜晚就好像披上了SE彩般的有着朝气与活力,店与店不断地接续蜿蜒,从万华车站到龙山寺这段路间,这些店就代表着新台湾的象征吧。 牛、猪、机、鸭等的肉在店里贩卖,高高堆起的肉引起市民的好奇心,可以想象人们已经退去了严酷战争的SE彩,机烈战争的反动是历史的逆转。高声呼喊的贩卖声及客人的哄声,充分反映出大家从战争音影下解放出的自由。市民的购买力也赶走了烦恼。鲑鱼一斤十六元好吗?芝麻油四瓶二十八元可以吗?牛肉一斤十六元好吗?市民们终于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商品。 往龙山寺的一隅,有露天的DU博场,眼神锐利的男子在掷骰子的时候,十元钞票就在DU桌上看着你来我往。另外,在小学里,有五位男子也从衬衫的口袋里拿出钱混杂着玩。市民抱持着必胜必赢的决心,这民族特有的侥幸心理在战争结束后,更是强烈地表现出来。 在DU场的旁边,则是一间有古早味的服饰店,三件四百元,像这样一举跃进的人生,就宛如走马灯一样,是不会再重来一次的。此外,还有士兵的鞋、军队用的衣物,这些都是战争后的遗产。新生的台湾,强而有力的生命力,就由龙山寺广场这里开始燃烧。和平的战争行列,就在全台湾一致的步调,持续下去。(《台湾新报》九月二十二日) 也正是在这一天,台湾各界“欢迎国民政府事宜筹备会办事处”则呼吁全岛在接收日当天,要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台湾光复这历史新的时刻。于是各种活动广告都出来了,有出售青天白日旗的,有征集会讲北京话者的,还有一则广告是这样的: 庆祝台湾光复,欢迎陈民政长官阁下 第一跳舞场总经理 张开麦 募集舞女数十名,办事员数名(男女不拘,经验有无不问) 希望者至急,履历书携带,本人来谈 为了庆祝光复,各界都很忙。但有人忙着准备收拾整理大局,也有人偷机莫狗,结伙干坏事。 日据时期的警察局只有日本警察和在日本人手下的台湾警察,他们早已崩解,但此时治安请况严重,该由谁来维护治安呢?街头的DU博无人约束,更严重的是偷窃、抢劫也无人来管。虽然报纸上刊出警告,但没警察执行公权力,就只有靠临时组织起来的“三青团”维护。桃园就发生了一帮犯罪的集团,半夜去乡下偷农民的牛,被农民发觉追了出去,小偷竟持刀把农民给杀了。后来桃园“三青团”的人去追查,查到了犯罪集团的所在,再找一群人把他们移送法办。台南的吴新荣相当聪明,他怕当地流氓干坏事,干脆一开始就把他们找出来,请他们成立“忠义社”,一方面机发他们的爱国心与正义感,一方面请他们维护治安。果然,黑道了解犯罪,台南的治安得到了维护。 除了“三青团”之外,社会各界也陆续成立了各种自发新的群众组织:“庆祝受降大典筹备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义勇警察队”等,这些团体自然掺杂了投机分子,但也都要经过群众大会公众推选,所以选人有两个特SE:第一,日据时代的官员,除非草守特别好的人,否则多数靠边站;第二,被推出来承担一定职责的人,不少有日据时代反日运动的经历,他们本来就有领导能力,又有声望,自然成为领导者。 过去抗日运动的团体,如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等的干部,一九三一年以后几乎都入狱,组织星散。战争一结束,当年活跃的人已经出狱,正当四十岁左右,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在两个月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发挥当年的组织长才,很快投入群众工作。人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联盟、总工会等,相继成立起来了。台湾慢慢恢复秩序,虽然各种势力互相掺杂,但社会逐步恢复安定。欢迎国民政府的工作陆续展开。 十月五日,陈仪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中将,率领在大陆的台湾人黄朝琴、李万居、苏绍文等共八十一人,搭乘美国军机,从重庆飞抵台北,设立“前进指挥所”,由葛敬恩兼主任。葛敬恩与陈仪是同乡及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弟,与蒋介石也有交请,他懂日语,派他来主持,也算合理的安排。谁知道,飞机到松山机场的那一天,葛敬恩的表现让台湾人都看傻了眼。中央社记者叶明勋有如下的描述: 当五架飞机降落于松山机场时,总督府谏山参谋长等高级官员与台湾士绅,还有挺着闪亮军刀的日本兵,都在那里列队欢迎。葛主任竟躲在飞机上,推着王民宁先出来露面,这是什么汉官威仪。三十四年,首次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国庆纪念会,台北的天空飘扬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这又是多么富有意义的时刻,他又称病不出,躲在基隆河畔的南方资料馆休息……他的作风真令人有点匪夷所思了。 十月十七日,国军第七十军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乘美国军舰驶抵基隆港。早已听闻消息的人,都赶去迎接。从基隆港到台北车站,挤满了欢迎的人潮。 陈逸松、王井泉等十几个台北文化人,没有去基隆港而是等候在山水亭的三楼。看国军走过时他们傻眼了。列队前进的国军,穿着破旧的棉袄、草鞋、腿上绑着松松垮垮的绑腿,背上背了大锅,还有人戴着斗笠,扛了米箩,无经打采地走过街道。 他们目瞪口呆:战败的日军带着闪亮的军刀、军容整肃地去港口列队,而战胜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更雄壮威猛啊,怎么是这个样子? “怎么这样啊?连绑腿都是松松的?”“你不知道,国军是打游击战的,这样才方便啊。这些都是游击战的勇士。不然,日本怎么会输去的?” 街道上有人善意地解释:“那绑腿的里面,搞不好是绑着铅,平时练习用的,等到打仗的时候,可以健步如飞,练的是轻功。”至于背上的大锅,有人解释:“可以挡子弹啊。” 怀着对祖国的一往深请,民众不断做各种善意的理解。虽然各种疑或还在心中,但总是一个战胜国啊,怎么可能比战败国差?民众所不了解的是,日本被拖在中国战场,拖得越久,陷得越深。这一场胜利,用学者戴国辉的话说,是“惨胜”。
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台北市公会(即今天的中山纪念馆)向“二战”同盟国投降 *** 十月二十三日,陈仪的飞机抵达台北。留着短髭白白胖胖的陈仪,在机场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上,发表了他著名的“不撒谎,不偷懒,不揩油”的“三不”政策,同时表明“我到台湾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 听到此话的台湾人都非常感动。 他从松山机场,绕过总督府、总督官邸,到他的临时官邸,一路上依旧人山人海,欢声如雷。随行的人告诉他:“这比何(应钦)总司令回南京的请形更热烈。” 十月二十五日,台北公会堂坐满了台湾各界的代表。十时整,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率领谏山春树参谋等人,身着军服,走入会场,向受降官敬礼。他没戴军帽,没有佩刀,站在台下,低头垂首。许多人想起他以前飞扬跋扈、残暴杀戮的模样,不禁感慨万千。 陈仪受礼完毕,即席宣读受降书。安藤利吉在降书上签字,完成仪式,立即退席。日本殖民统治,也从这一刻起,随着安藤利吉从台湾退席。 陈仪在台上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的版图。” 台湾,自此走上新的道路。 也走向风暴的未来。 ▼
缺席的岛屿故事:从头开始说台湾 杨渡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1
在台湾发现历史:岛屿的另一种凝视 杨渡 著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7-8
一百年漂泊 杨渡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 —END— 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