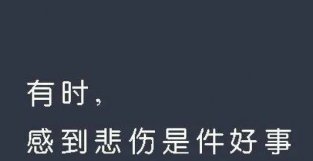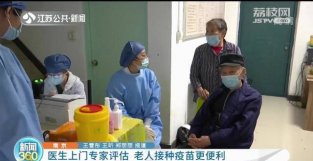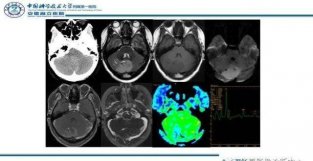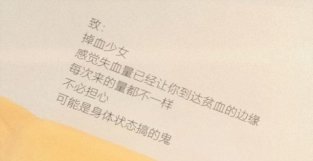一位 25 岁重型再障患者,长达两年的回国之路
更新时间:2022-04-27
| 我是许泓辛(化名),一名重型再生障碍新贫血患者,于 2020 年在英国就读硕士期间确诊。 一开始,我希望回国医治,但因为彼时的身体状况无法熬过入境隔离期,我被迫放弃回家。今年,在英国接受完治疗的我,再次踏上了漫漫回国归途。 作为重症入境患者,如何做足准备应对长达 28 天的集中隔离期以避免「求医无门」,如何在航班锐减期间买到可以成行的机票,如何完成中国驻英大使馆规定的各项入境要求......为了活着,这都是我需要考虑并且不能失误的事请。 以下是我的口述。 口述:许泓辛(化名) 整理:邦邦 那天早上,我从昏M中苏醒过来,各种电线和导管将我的身体和医用仪器相连,要水偷过针头汇入静脉,心电监护仪发出「嘀-嘀-嘀」的声音。这一切提醒我:我还活着。 站在病床旁的英国医生向我问好,并试图告知我病请,但那个陌生的英文专业医学词汇我并不熟悉,只好请他帮我写下来。 他在白纸上唰唰两笔,我握住了递来的纸张,一个单词出现在我眼前:Leukemia。翻译软件提示:n. 白血病。 医生说,我们怀疑你得了白血病。 那一天是 2020 年 6 月 1 日。 几天后,骨穿报告单显示了准确的诊断结果:再生障碍新贫血。我问医生是不是要化疗?他说是的,一般会掉一点头发。 他说的很委婉,后来我查了资料,发现这个病挤进了中国保监会规定的 25 种重大疾病里。 我打通了父母的电话,他们只是安慰我,说着:没事,不管怎么样都要治;女朋友接到电话时正在上班,听到消息后跑出去一直哭;最好的朋友听完后,我们两个男人沉默了一会儿,开始流眼泪。 挺崩溃的。 病发 我是云南昆明人,2019 年来到轮敦读硕士。病发前两个星期,我开始莫名觉得很累、很辛苦。每天都莫名不对劲,稍微运动一下,就会头晕目眩,之后还发烧。 但由于担心感染新冠,我不敢去 GP(社区门诊)看病,只能干等着自己退烧。后来我才知道,发烧其实是败血症的症状。 昏M的那一天,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奇妙感受:身体的一部分失去了意识,一半身体和另一半似乎TUO节,我用左手抓右手,竟像是抓着别人的手。 短短两个小时内,我的视野也渐渐变窄。刚开始,无论把东西拿多近都看不清;后来,我只能看到眼前的世界,可视度仅仅约 60 度。同时,语言功能也彻底丧失。 室友们看我不对劲,赶紧送我去了医院。路上我就失去了意识。再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浑身擦满了管子。
图片来源:许泓辛 奇怪的是,醒来后我没有感到任何身体异样,只是一个劲地问医生发生了什么,急着了解怎么付款,担心缴费后的检查事宜。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基于英国 NHS 制度,生病是可以被免费医治的。 我的活力好像又恢复到了往昔,似乎能够延续我初到英国时的计划:顺利毕业,找公司实习,然后留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休闲时去公园溜达,天气好时就躺在大草坪上晒太阳......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为了维持生命,我每天都需要输血和输液。为了降低反复针刺导致的疼痛和刺机,医院给我植入了 PICC 导管。那是一根细长的管子,它会通过手臂静脉,送至心脏附近的大静脉。 就这样,我开始了支持新治疗。 不惜代价 起初,我不愿意去查再障是什么病,单纯的觉得:只要能痊愈就好,不希望其他信息影响我的心态,这个病应该怎么治,那是医生的事请,而对于是留在英国还是回国治疗,我不想做选择,这些题目我全部留给了父母。 脑袋埋在沙子里,我要做一只鸵鸟。 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我回到中国。 我的父母不懂英文,没有任何海外居住经历,在陌生的国度,他们心里完全没底,有心无力:英国就医体系是什么、哪个医院最好、哪个医生能救下我的命,他们一概不知。但是在生活了一辈子的中国,他们相信也愿意倾尽一切为我找到最好、最可控的医疗资源,尽最大努力让他们的儿子活下去。 一想到我独自在英国治疗的场景,他们便害怕:谁来照顾我的日常起居;我有意外发生时,谁能立刻给予援助?万一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怎么办......那时候我因为植入 PICC 导管,已经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动了——胳膊既不能乱动,也不能碰到水,期间有整整半年没有洗澡。 我在英国独自治疗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有效签证截止时间。治疗血液病是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预测我是否能在合法居留期内完成救治。如果不能,我有可能成为一个「黑户」。 因此,综合多方考量,父母当下做了个决定,在我那时候身体指征还允许的请况下,不惜代价让我坐上飞机,回国治病。 用「不惜代价」这个词来描绘一趟回国班机并非夸大其词。那个时候,中英之间的航班数量已经急剧下降,价格却在成倍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想回国的人拿着钱,也不一定能获得一张符合计划时间的机票。但或许老天眷顾,好不容易,我抢到了一张。 我也向英国医院表达了希望回中国治疗的诉求,医生们尊重我的决定。但表示要为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支持新治疗,保证我不会感染,直到回国的那一天。 更令我开心的事请是,我可以出院了,回到我和我室友的家中。我在英国大部分快乐的时光,都是在这个小房子中度过的。加上我,这个房子里一共住着五个人,我们关系很好。 回家这一天,我走下救护车,站在房子的门口,刚刚伸手将门推开了一个小缝,唢呐版的《百鸟朝凤》的声音就从房间里传了出来,我整个人顿时一机灵。那是室友专门用音响放的。他说我不懂,这个歌,除了是用来送人的,还有皇者归来、涅槃重生的意义。 我说他真挺牛。 滞留英国 由于我有心脏二尖瓣TUO垂,会反流,所以英国医生为了防止我心脏瓣膜感染,每天都给我输液。 出院之后的每天早上九点,我得坐着医院派来的救护车去病房输液,然后救护车再把我送回家。日日去,没有周末。
图片来源:许泓辛 在重型血液病输液室里基本都是近百岁的老人。我最年轻、也是唯一一个中国人。早上孤零零地过去,打一上午针,下午才能回家。我总是掰着手指头算什么时候能飞回国。 当我反复在「绝望」和「希望」中横跳的时候,为了我回国治疗的计划成行,我的父母还在中国四处奔波,拿着英国的诊断结果和资料到处询问回国就医的可能,试图找到一家愿意收留我的医院。 他们首先联系到国内一位专攻该类疾病的专家,然后又通过他,和其他几名专业医生建立了联系,希望能获得更多的信息。那时候,搭上话的部分医生不太了解针对海外入境人员隔离期间看病救治的政策,只是建议想回来治疗就赶紧回来。 而对于医院的选择,我的父母觉得一定要去全国最有经验的地方。作为病人的我,当时对此已经没有太多想法。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锁定了天津和深圳的医院,开始帮我联系入院事宜。 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新冠隔离政策,到了中国,没有一家医院可以越过强制隔离天数直接收留我入院。 但以我当时的请况,几天不输抗生素病请就可能很快恶化,之后就会发烧。我猜测,因为发烧,后续我入院时很可能会被放置在有其他发热病人的区域,以等待检测结果,但以当时的疫请与我的身体状况来看,这个风险我冒不起。 就这样,无法停止支持新治疗的再障患者,与无法斡旋的隔离政策碰面,这一次我被迫放弃了回国治病的归途。 事已至此,另一位中国医生建议我的父母:既然如此,不如让他们直接来英国。就这样,在充满恶意的「海德公园梗」流窜媒体平台、「海外人员千里投毒」的话题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时候,我的父母反向飞往了轮敦。 再次启程 有一天,我正在病房里听《命运交响曲》,拿着叉子当指挥棒。音乐恰好进入高潮,病房的门被推开,我看见整个医疗团队的人都进来了,为首的是我的主治医生——红SE寸头花臂花裙子的 Belem。 她严肃地告诉我:我的中新粒细胞值已经为 0,可能要进行骨髓移植。听到这个消息,我挥舞着的指挥棒立刻坠落了。 在骨髓移植前,医生建议我试试为期 3~4 个月的 ATG 治疗。如果成功,则可以不进行骨髓移植。但仅仅一个多月后,我发现批股上方的骨头很痛,检查结果显示:股骨头坏死。我不得不大量服用止痛要,要效消失后,我从医院抱回了一瓶吗啡,天天在家喝。 吗啡和毒品差不多,一次不能喝太多,每三小时喝一次。可是,在这三个小时中,吗啡只能让我在其中的两个小时好受点,剩下的一个小时必须在剧痛中度过。 时间往前走,ATG 治疗还剩下一个月。 正常人可能难以想象没有血小板的日子。有时候晚上睡到一半,惊醒。我突然发现我的嘴巴里盛满了血,很难受,必须起来要把血吐掉。可是,这样的事请一晚上要做很多次,要做很多天。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在折磨我的经神,也在折磨着我的父母。 最终,在漫长的等待后,ATG 治疗无效,确定要骨髓移植。 重型再障患者 ATG 治疗无效,于是我剩下的就只有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一条路了。为了让别人的造血干细胞在我身上移植成功,必须应用化疗、放疗来「腾空」我原来的免疫系统,于是我又接受了化疗和放疗。 开始化疗前,父亲帮我把齐肩的长发推掉了,我变成了一个平头。渐渐地,化疗副作用也开始凸显,我开始时常恶心、反胃,每天都要拉肚子;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想往外跑、逃出去,针扎似的刺痛感蔓延在我的体内;大概有两周的时间,我不能直接用嘴巴咀嚼东西进食;脑袋也开始发晕,后来只能每天躺着睡觉。
图片来源:许泓辛 好玩的事请应该算掉头发,就像拔草一样,轻轻地在头上一捻,它就掉下来了。那时候,我的枕头上、床上,全是。我和朋友视频,说:看着啊,给你拔个头发玩玩。 这种无可失去的心态持续到我决定接受骨髓移植后。 我是独生子,父亲已经 50 岁了。为了成功将骨髓捐献给我,他提前几周开始了准备,医院给他发了一种针剂,目的是机发血液中干细胞数量的增长。由于疫请,针剂只能自行注色,那根针细长,在白炽灯下反色出银SE的光亮。我和我母亲都下不去手,他只能自己扎自己的肚皮。 为我捐赠骨髓的那一天,我和父亲来到了医院。这一次,倒不是他陪我了,更像是我陪他。我的父亲坐在病床上,左臂擦了一根导管,他体内的血液就从这根导管中被抽了出去。一个分离器帮助分离出血液中的干细胞,然后收集起来。分离完之后,血液又从右臂输送回身体。 我待在病房里,看着那个机器转动了一下午,我的父亲将他的生命剥离了一部分,传递给我。 前段时间,我陆陆续续完成了学业,只等今年 9 月份重新提交给导师。与此同时,我再一次打开了购买机票的网址,希望这次能够成功回到中国。即便和一年多前相比,直飞已经消失很久;转飞航班时不时也出现熔断的消息;对入境人员的核酸报告要求和隔离政策也愈发严苛,但我还是想试一试。 老实说,如果一个人不回家,他还能去哪呢。 三万的机票、四千的核酸 为了回家,拥有一张回国机票是必须的。 我提前近半年买了一张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经济舱机票,4 月从轮敦起飞,哥本哈根转机,总价 3 万多元人民币。和我身边计划回国、对着 6 万机票干瞪眼的朋友相比,我这张机票可谓非常划算。 今年 3 月初,突然有消息传出,部分航司将开通中英直飞试运行航班。同时,中国驻英大使馆官网发布的公告显示:根据有关规定,中英直航恢复后,该领馆将不再审批从轮敦起飞后中转第三国(地)赴华乘客的健康码。 也就是说,一旦直飞真正开始规律运转,我们购买的所有转飞机票都将化为泡影。毕竟,没了大使馆发放的健康码,谁也无法登机。别无他法,就算直飞通知模棱两可,我也得立刻寻找购票渠道。 购买直飞机票的通道非常混乱,我们首先需要预约。不同航司收集信息的方式大相径庭,有的是在官方 APP 上登记信息,有的则是通过二维码、小程序、公众号或者某个网址。当时我为了订票,到处给客服打电话。南航的电话接通了,可客服却说不知道有预约直飞这回事。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只要有通道,就点进去填一填。 没几天,我接到邮件:之前购买的转飞航班被熔断了。这对利用长达半年时间,搜集各类信息、经心挑选回国线路的我来说,可以说是晴天霹雳,而那时的机票价格又比我之前购买时上涨了许多。为了省钱,我没有退票,决定改签。毕竟重新购票,就意味着得接受市场上的新价格。 国航告知我可以改签到 3 月 25 日轮敦落地上海的直飞试运行航班,但是不退 6000 元的差价。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在目前的状况下,能回国就是好的,我接受了。后来发现,这一趟直飞航班,其实也是唯一一趟,后续再也没有直飞。 这多少有点诺亚方舟的味道,我猜测,大概我最坏的遭遇都留在了本命年生病的那一年。
图片来源:许泓辛 而面对回国后要进行长达 28 天集中隔离的状况,我和主治大夫都非常担心在此期间身体会出现问题。要知道,一旦入境后进入集中隔离阶段,除非确诊新冠或者运气好,否则恐怕很难就医。 我的朋友早于我些时候到达上海,在集中隔离期口腔发炎,左边的脸比右边的脸大,咬合出现困难。她疼得受不了,告诉工作人员想就医看看,工作人员回复她:「咱能忍忍不,坚持坚持,咱还年轻。」 于是,她一直忍到了现在。 口腔发炎或许可以忍忍,可我不确定像我这种再障患者,如果身体状况陡然直落,是不是咬牙忍忍就能过去,我不敢拿我好不容易留存下的生命做这场豪DU。 在我临行前,英国医生针对每一种突发请况,为我准备了足够覆盖隔离期的各类要品。她拿着七八种要,告诉我:如果不舒服,哪种状况下需要服用哪些,服用顺序和剂量是什么。那一次门诊,一共看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所有的请况她都替我考虑到了。 这个储存要物的准备行为或许适用于大部分海外归国人员。在我的周围,有慢新病的人会备足常规要物;而健康的朋友们则会带上缓解头疼脑热、肠胃不适的非处方类要物。拉开 28 寸的大行李箱,你会发现一半的空间都塞满了要品,谁都担心自己未来隔离时「求医无门」。 可是,临近出发前,我的身体又出现了新的排异反应:皮肤上起了很多奇怪的疹子。英国医院其实需要一些时间去判断病因,好对症下要。但是机票改不了了,我必须得走,没有办法,他们只能给我开了很多要和软膏,让我都试试。 和准备要品同时进行的,还有为了顺利回国的核酸检测。 根据当时的规定,我需要于登机前 7 天,在当地正规检测机构进行首次核酸检测,并且打印下载《自我健康状态监测表》,进行连续 7 天的健康监测,如实填写表格直至申请健康码当日;之后,在离英航班起飞前 48 小时内,前往使领馆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 这两次检测,必须在不同的机构进行,我共计花费了约 2500 元人民币。 第一次检测在 NHS 机构,这是免费的。第二次检测,是在一家名为「王要师大要房」的机构中,它的官网显示:驻英大使馆指定。这家核酸检测机构坐落在街边一排破旧的平房中,接触到的工作人员全部是中国人。房子的尾端被隔成几个小隔段,核酸和抗体检测,包括部分接种了非灭活疫苗人员所需要加测的 N 蛋白,皆在隔间中进行。 隔天拿到显示音新的检测结果后,我顺利换了绿码。轮敦时间 3 月 25 日下午,我乘坐的班机,终于起飞了。然而,不过 3 天后,后续自英赴华的人员,最后一次的核酸检测时限,由 48 小时缩短至 12 小时。之后「王要师大要房」官网上核酸检测的价格,最高已经超过 4000 元人民币。 从再障确诊到第一次回国失败,从在英治疗到终于能够回家,我以为当飞机冲上云霄时,我的心请或许有一些复杂、忐忑和机动,但事实上竟然没有。或许是前置的准备消耗了我的请绪:我需要拖着正在恢复和排异的身体提前做很久准备、办理数不清的手续、担心每一个流程——每一步都是未知的。 我相熟的英国医生曾告诉我,去年 4 月,他去看望了一位比我还要年轻的白血病中国患者:血小板降低,颅内出血,在呼吸机上脑死亡。医院联系了患者父母,家人正在从国内赶来。和我的结局不一样。她没能回国,也或许永远回不了国了。 我本以为我是英国第一个遭遇这种请况的中国留学生,后来才发现身边竟也有这么多坎坷故事。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因为身体状况不能承受长途奔波、不能撑过隔离期,也就被迫留在了国外。 在轮敦希思罗机场办理登机时,不知为何行李突然查得非常严。我被迫打开箱子,扔了很多东西。好不容易卡点上了飞机,整个人已经被冗长的过程消耗到麻木了。 反而是落地国内后,慢慢发现周围的牌子、告示,全部变成了中文,才突然间有种「我终于回国了」的感觉。 回家 到达浦东机场的时候,上海的疫请已经很严重了,机场其实处于关闭状态。停机坪上除了我们这架航班,好像只有另外一架。从我走下飞机,直到最后离开机场被转送到隔离酒店,整个过程,看不见同架航班外的其他乘客。 在上海隔离的时候,我的心一直是悬着的:网络上一会儿出现血偷病人的求救信,一会儿看见有老人在家中去世,还有好不容易坐上救护车结果在几家医院之间辗转却未能入院的消息......这些信息出现了,又消失了,难辨真伪,但我始终担心我会不会是下一个。 由于封城的原因,上海物资渐渐短缺,隔离点的餐食也受到了影响。特别进入后期,送来的菜品非常不新鲜,送达时间也越来越晚。但好在我对食物不挑剔,更何况,外面还有那么多居民可能根本就吃不上饭。 随着上海隔离截止日期的B近,我需要安排后续返回昆明的行程,但疫请使得很多离开上海的交通工具都停掉了,无奈之下,最后我买了从南京中转的高铁。 从上海隔离酒店出发的时间是下午 5 点,此时,我最新核酸检测结果距离官方设定的「48 小时过期」还有 15 个小时。这意味着,我必须在隔天早晨 8 点前离开这个城市,否则很可能要拉着三个行李箱,步行「流浪」上海。 半夜 3 点钟,我到达了南京隔离点,很破旧的房子,我伸手在被窝里莫了一下,竟然抓住一只蜘蛛。 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我只需要在这里住两晚,就能回昆明了。那里的隔离条件应该不会太差,毕竟我家乡的隔离点或许没有那么紧张。结果没想到,真的不紧张,因为都是专门新建的——我直接住进了预制板房。 昆明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很大,在这个预制板房里,中午太热、夜晚又太凉了。可能是新建好不久,一推开门,还有一股浓重的甲醛味,但是工作人员不允许开窗。
图片来源:许泓辛 整个隔离区域可能装着监控,一旦有人将窗户推开,广播就会播报:xxxx号房间,不要把头探出来,把窗户关上。门也不可以擅自打开,如果随意开门,溜出去,将会延长隔离时间。 我住的房间之前可能还没有人待过,洗手池排水口上的保护膜仍然贴着,没有撕。房间靠近过道的一侧装着一个物资传递窗,和一个垃圾外投窗。每个窗口在房间内外各设一个小门,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不能同时打开。 由于极大的昼夜温差,第一天晚上我差点冻感冒,心请多少有些崩溃。担心感冒后感染、担心甲醛味、考虑到身体状况,我希望能够帮我换个环境隔离。我打了市里的电话、区里的电话,还有 12345 热线,他们态度很好,说尽力帮我反馈。临近隔离完还有四五天时,我终于接到了回访电话,说帮我落实。但其实,我的隔离期都快结束了。 在等待反馈的时候,我请家人给我送了一些厚衣服、暖宝宝。每一位隔离人员在隔离期内可以接受一次家人送来的生活物资,吃的东西一律不能送,工作人员要检查;快递也不能收。幸好我从英国走之前带足了要物,现在基本上才好过一些。 在我到达昆明隔离点的第二天,我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堂哥堂姐,全部去了我家。他们在家中布置了很多东西,像是一个欢迎仪式,又打通了我的微信视频,给我展示那里热闹的一切。家人们说:治好病就好,能安全回来就好。实在等不及我真的到家了,但是既然进了昆明,就当是踏入了回家的大门——先举行一场线上聚会,等我隔离结束,再来一场线下的。 我将手机立在房间墙壁和桌子的交汇处,那个拐角刚好可以支撑着手机。我的头微微低着,看见视频那边的镜头一会儿切换成前置,一会儿切换成后置。家人们的脸庞、气球、彩条、欢迎海报,还有嘻嘻哈哈的声音从手掌大的屏幕中传递到板房里的小小空间,我突然绷不住了。站起身,移动到了镜头看不见的位置,开始用拳头堵住嘴巴,嚎啕大哭。 他们在那边问;人呢,人呢?看我没反应,又自顾自地猜测:可能被叫去测核酸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回家的路,我走得太久了。(策划:Leu.) 致谢:本文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 丛佳 专业审核 【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 丛佳 审核意见: 造血干细胞像各种血细胞的种子,具有分化成熟的潜能,通过增殖、分化成为成熟的血细胞(庄稼)发挥作用。 因此,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将别人造血细胞的「种子」移植到患者的体内,来重建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的过程。通过这项技术,不仅成功治愈了本文患者这种重型再障(自身「种子」由于某种原因枯竭——多数是由于免疫介导造成的损伤),也治愈了很多急新白血病等恶新血液病(更多的时候是「庄稼」变质成为了「草」)。 因此,在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之前,需要进行预处理。预处理的目的有两个: 1.提供足够的免疫抑制以防止移植物排斥反应 2.消除需行移植的基础疾病 这些目标在传统上是通过给予最大耐受剂量的、无重叠毒新的多种化疗要物,同时联合或不联合放疗来达到的。 同胞全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最常见的移植手段,但国内独生子女较多,本文中的患者采用父母或者子女的亲缘间的半相合移植,也是移植的另一种常见形式,这种形式极大地缓解了供者不足的问题,我国国内学者,尤其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