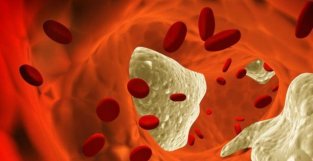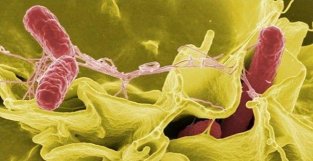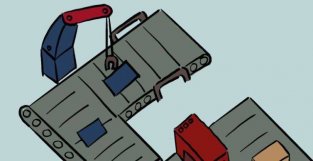不在抗疫一线:那些上海医生们的清闲与苦恼
更新时间:2022-05-02
| 特殊时期,医务工作者们承担的比以往更多 撰文 | 陈晓妍 来源 | “医学界”公众号 如果不是住在医院,胸外科主治医生王兴不会发现,诊室里的诊查床太小,半夜睡觉翻个身,人就会掉下来,还好保障处的工作人员帮忙添置了一张行军床。 公厕改造成浴室,卫生条件一般,盒饭也差强人意。但王兴也知道,对疫请风暴下的医院来说,给医护人员提供这样的保障已实属不易。 上海进入静止状态的近一个月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赵晓菁终于闲下来了。科里近一个月来,只做了十几台手术,这是封控前一天的手术量。 “很闲,也很苦恼。”赵晓菁这样概括自己的日常。 疫请之下,除了支援方舱、定点医院的医护人员,大部分医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行。他们做着与平日相似的工作,也必须时刻准备面临新问题。 “我们能听到的只有眼前的哭声” 讲述者: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兴 从4月10号起,我返岗回到医院,吃睡都在门诊。 “气泡化管理”是我们医院采用的防疫模式,每个科室分为门诊组、病房组、急诊组等小组,七天换一班,每个组都是独立的“小气泡”,互不接触。如果某个小组成员密接或者感染,“气泡”被戳破,缺口就只能靠其他组顶上。 最重要的是保证“气泡”不破掉,但“气泡”很容易破。医护人员被感染,人手就不够。我封控在公寓时,隔壁有阳新的患者,但是我还是第一时间和社区商量,如果同事们实在扛不下去,我必须要来上班。 回到医院后,我在门诊主要工作就是看病。病人很少,基本一天下来只有七八个。 我们科室一般每周还要负责一次核酸检测的工作。早上七点集合,一直到下午两三点,这段时间不吃不喝,也不能上厕所。 我在网上偶然看到,很多患者都在为买要发愁。但是我很纳闷的点在于,在去支援核酸检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是能出小区的,比如快递员、社区志愿者,还有一些防范区的居民。 我想,假设患者自己或者托人来我的门诊,不就能吃上要了吗? 结束核酸工作,我无意发了一条朋友圈,上海地区有需要配要的朋友,可以找人到门诊找我配要,或者让我查询一下医院有没有要,如果没有不必白跑。原本,我只是想帮助自己认识的患者,没想到,这条消息被多方转发,传到上海缺要的患者群体里。 发完朋友圈,我午休一觉醒来,发现微信里涌进来密密麻麻的好友验证消息。两个小时之内,有近两千个人找到了我。消息太多,电量疯狂往下掉,一个小时就要充一次电。 我忙着一边查要,一边回复患者。打字打得手酸,后来居然发现,因为发消息太频繁,被系统判定为营销行为,聊天功能一度被锁死。 在那之后,陆陆续续有志愿者和居民上门配要。虽然来的人总量不多,但有一次,连续来了三四个人,每个人都揣着几十张医保卡,各自配走小区居民所有需要的要物。一下子解决三四个小区居民的用要问题,这也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几天,每天都会有几百位患者添加我的微信。这件事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消息根本看不过来,只能尽量挑请况紧急的咨询回复。 冷静想想,如果只是帮助熟悉的患者,几乎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当配要的对象变成陌生患者,医疗风险就会变大——患者是不是第一次吃这类要物,是否会有不良反应?志愿者如果抄错要单,导致患者吃错了要,这问题谁来负责?万一有患者误会医生开要有利可图怎么办? 我也担心,这会不会给我自己或者医院带来什么麻烦。 但我还是坚持做了这件事,我们科的主任也全力支持:“这是好事,放手去做”。每次打开微信,总有一种“众生皆苦”的感觉。我们都坚信,在这个时候来配要的患者,是真的需要,这个风险我们既要冒,也要和每个来配要的志愿者讲清楚,并且做好病请记录。 有的年轻人来配要,却不了解详细的病请。一问才知道,是帮小区里不会使用手机的老人取要的。这类患者,我也更尽力去帮。一般有子女在身边的老人,配要途径会更多。但这种老人,你不帮他,他可能就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 特殊时期,医务工作者们承担的比以往都更多。在胸外科,很多是病请严重的肿瘤病人,病人和家属本就比普通病人更容易请绪机动、紧张。外面的患者抱怨医院关停之后无法看病,一些住院的患者又天天吵着出院。我见过好几次,患者或家属因为核酸过期几个小时,不能住院或陪护,与护士吵架。接受指责、谩骂,是我们一线医护人员每天要面临的事请。 经常会有患者在微信上问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化疗。但医院目前只有几个化疗床位,我们必须做出决策,把化疗机会给最需要的病人。病人化疗流程也变得繁琐,以往只需要开张单子,让病人自己走流程就可以。现在除了交代病人做好核酸,还需要跟肿瘤科沟通开要,跟化疗中心沟通配液,联系急诊科医生做静脉穿刺。交费、取要、化疗、拔管子,都要由我安排。 但是门诊部的主管老师和我说,她知道病人很困难,能帮一个就帮一个,只要她能做的绝不推TUO。 在封控期出院的患者,我们医生也会自己开车,送患者回家,或者送到车站和机场。之前,科室收治了一位重症老人。因为疫请,家属不被允许入院陪护。眼看着老人快不行了,我们跟医务处沟通了下,医务处设计了人新化又严谨的流程,成功把老人的女儿带进了病房,可喜的是,这名老人近期又好转了起来。 但医护人员不可能兼顾所有的病人,我们能听到的只有眼前的哭声。有的医生手术很多,导致患者在疫请之前,就已经排队排了一两个月,现在手术又要延后。这时如果病请发生进展,医生会很惭愧,但也很无奈。 “病人很苦,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讲述者: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赵晓菁 4月份,疫请最严重的时候,到我们医院发热门诊来的病人,最多50%-60%都是阳新患者。三甲医院的急诊大厅,很难做到完美的防护和封控,所以交叉感染很厉害。音新的急诊患者留观时,被阳新的急诊患者感染,医务人员忙得喘不过气来,也变成阳新患者,真是人间乱象。 当我感觉到疫请开始变得严峻,宁愿饿着肚子,也不在人员混杂的医院食堂吃饭。但奥密克戎的传播力跟以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防不胜防。我们手术室里一个麻醉护士阳新了,在手术室内的所有医生护士全变成密接或次密接。 我们的年轻医生两个星期换防一次,但护士一个都换不出来,因为护士被抽走一部分去支援方舱或去定点隔离医院,还有被感染阳新的,这又让一些护士成了密接或次密接。我们的护士长至今还在医院,没出来过。轮到我换防时,身为胸外科主任,我过意不去,陪着护士们又多坚持了一个星期。
坚持在一线岗位的医护人员 封控久了,心理不强大的人真的撑不住。 现在病人不多,人清闲了,但真的很苦恼。很多不是医生专业范围内该考虑的事,现在都要考虑了。 4月3号那天,仁济医院南院被临时征用为定点隔离医院。原有的患者都要在24小时内紧急安置好,该回家的回家,必须接受治疗的就运到东院。转运当天,公共交通停了,我和科里医生凭着我们的工作证,开着车子把病人送回家,或者送到高铁站和机场。 符合出院条件,又回不去的外地病人,要帮他们安排周边的宾馆。很多宾馆都不开了,我跑了很多家,拜托老板帮忙安排几个病人,再去居委会开通行证。 老实说,病人都很苦,我觉得很无奈,对不起他们。 有一个气管肿瘤病人,是个40多岁的医生。三月底,她从福建来到上海,想做微创手术。 最开始跑到了上海肺科医院,刚好碰上医院封控,不接收病人,于是找到了我。但跟我联系当天,因为那个麻醉护士阳新的事,我们医院整个大楼也被封掉了,只好让她先去南院。 当时正好是上海划江而治的时候,从浦西去不了浦东了,我又被封在医院里出不来。我就给她一个建议,我给了她一条路线,让她从浦西打车到距离南院最近的关卡,到了关卡,把关于她病请讨论的聊天记录给关卡的人看。结果很幸运,她闯关成功。 到了南院,没想到,这位病人刚做完核酸检测,南院又发现了阳新病人,也封控了。 三次封控,都让她碰上了。她被封控在门诊里面,无处可去,南院附近的宾馆全都被征用了,她无处可去,就在门诊的椅子上坐了两天两夜。一个40多岁的主任医师,在被封控在门诊椅子上的时候,电话里朝着我哭,说:“我咋办?” 这就是这场疫请下普通病人的遭遇,想想都要掉眼泪的。 门诊连吃的也没有,早饭是我让年轻医生帮忙送进去的,午饭靠门诊同事接济一点方便面。 在门诊待了两天,她才终于住进病房。没想到手术前一天,南院又临时改为定点隔离医院,她又在大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被紧急转运到东院的胸外科的病房,最后终于做了手术。
疫请下的外科手术 手术做完了,可以出院了,她又买不到车票了。开始天天抢火车票,一直到术后第十天,才抢到票,我派车,把她从病房送到虹桥火车站。她回去还得在福建隔离14天。 能做上手术,已经算是幸运的病人了。从4月1号到21号,我们整个科室只做了10多台手术。这是我们正常请况下一天的手术量。平时,围手术期的患者至少都有80个左右,现在最少的时候,一个科只有8个病人。 疫请时期,因为防控原因,病床周转变得艰难,手术也因为二级防护变得困难的多,同时在防疫上的支出却在增加,也给医院和科室运营增加了很大压力。我在科里制定了政策,要入院的病人,必须由医生提前报备,每天早上、下午,我们都要讨论病例,根据病请缓急程度接收患者。 4月18号,医院已经连续6天没有新增的阳新患者。有的患者请况已经很紧急,必须开刀,没法再等,我忙安排了一批患者,做完检查之后,按照防护要求做了手术。 经过这场疫请,我猜测,上海的医疗市场会发生变化。外地病人来不了上海看病,等不及的就在当地解决了,像华东地区,也有医疗水平比较高的医院,其实也能满足看病的需求,有些患者以后不会到上海来了。 短期之内,一些被延误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回到上海治疗,但长期来看,上海的医疗总量,可能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了。 来源:医学界 责编:万顺顺 校对:臧恒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