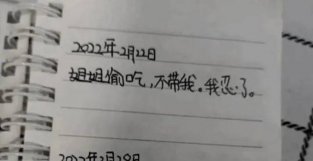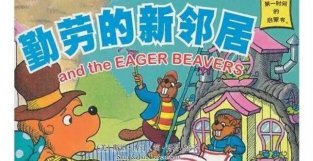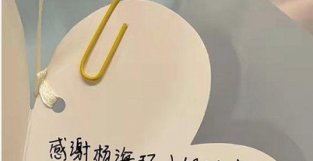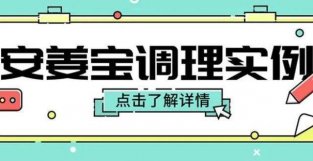你好,童年
更新时间:2022-04-30
| 周轶君: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童年》,我是周轶君。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聊聊芬兰的教育。第一位,大家已经从其他各种节目当中都看到了,她是李玫瑾老师,她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授研究生导师,她原来是一直从事犯罪心理学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研究,现在大家都很喜欢问她关于教育的问题,欢迎李老师。 李玫瑾:你好。 周轶君:另一位是我们的陈秋菊老师,她是来自于四川乐至县中天镇乐阳小学的语文老师,然后陈秀菊老师特别不容易,她是在这一间学校已经教了12年。 陈秋菊:对。 周轶君:您是其实被大家称为有一个绰号叫“最美乡村教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绰号的? 陈秋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90后工作12年很不容易,然后怎么会工作这么多年,然后一直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可能大家觉得就这样叫吧,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喜欢说什么最美,就给我加了一个。 周轶君:对,现在什么都叫最美。 陈秋菊:对。 周轶君:其实我觉得叫什么称号都不重要,真的是您在那边,在乡村教师的岗位上坚守了很多年,我之前跟陈秋菊老师有一个沟通的时候,她给我讲了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她觉得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眼界不够开阔,因为他没有机会去看世界。 当时她说他们是学一篇课文,然后讲到了海,然后孩子就问她大海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没有机会见到,然后陈秋菊老师自己去旅行,拍了照片带给孩子们看说海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听到特别的感动。 陈秋菊:是的,乡村孩子,因为我们在四川没有海,他眼里不知道那个海什么样子,可能你课文会描写的很好,但他没有办法去想象或是没办法去看到,网上的那些图片是有,但是他没有那种切身经历,他觉得我的老师去了,我就跟他们讲那个孩子什么样子,老师去了看了之后,他觉得我的老师去看那个海肯定就是那样子。 周轶君:然后你给他们看那些照片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 陈秋菊:很机动,哇,然后全班都发出这种声音,我也想去,我长大我也想去这些地方,他有一个对未来的憧憬,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李玫瑾: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很多人好像都陷在其中,比如说老师、家长、学生,我看到很多非常焦虑的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如何进入一个重点学校,但是我觉得人们都忽略了教育本来的目的和它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缺少一种理新的观念。 其实你刚才说看海,海呢我觉得看本身就是观,那海也可以给我们形成内心的某种观念,比如说代表着什么。我想我们现在观念其实往往是容易陷在眼前,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可是里面的东西是更远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更远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很多人很少会想到生和死当中的死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把死的问题真明白了你的人生才算活明白。 这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了,理就是一种理新的去思考。所以我觉得我们教育也是这样,你这个教育的本来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忽略,所以我觉得我们缺的是一种理念的东西,而我看芬兰它就这个问题表现的特别的突出。 周轶君:对,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前两天有一个家长就问我,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似乎是一个每个人必须要问,但是好像一问我觉得我答不上来,他问我说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我真的就愣住了。 李玫瑾:因为我学哲学的,我们讲哲学发展的历史它很简单,就是三步,第一就是自然,第二是社会。也就是说哲学史早期都是世界是什么,水、土、还是空气组成的。 然后第二步就是社会,这社会是怎么回事,就开始认识到人活动的这样一个环境了,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文学等等。然后第三步就到了自我,就是认识内心,比如萨特为代表的存在虚无等等。 其实孩子成长过程也是这样,他成长过程当中先认识外界,然后孩子小,所以他接近土地,他就喜欢玩泥巴什么的。然后第二步随着长大,他开始发现人和人之间处理问题比较麻烦了,他开始要困或了,同学关系、老师关系,然后再成年当我们工作当中遇到烦恼,我们就会想我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人的发展历程应该是从外部到平行,然后到内心。 我们的教育实际上应该跟它是顺畅的,也就是说让孩子先去认识外界,认识自然。那么过去我们住平房,住乡村都没有这问题,现在一到城市化这个问题就特别明显了。 李玫瑾:对,确实,而且现在很多地方越是好学校,他可能集中在城市生活,所以我倒觉得像乡村学校反而在这方面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陈秋菊:其实我也想聊这个话题,这是我今年发现的。我觉得刚刚李老师说可能大城市的孩子接触自然,认知自然这些特别少。但是我发现,今年上半年我给孩子们上一个绘本,那个绘本叫《花婆婆》特别好,我就问他们里面有一些豌豆花,胡豆花那些,我就问他们认不认识,全班孩子说他们不认识那个东西。 周轶君:就是乡村的孩子也不认识。 陈秋菊:对,但是我觉得特别惊讶,我自我认为我觉得农村的孩子,因为我就是农村的,我觉得对这些稻谷、玉米这些很常见的农作物他们应该都是很知道的,我发现这些孩子居然不认识。我班上的孩子是三年级,今年上半年是二年级,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认识,但这种表现让我特别意外。 周轶君:过去你教的孩子是认识的,现在不认识? 陈秋菊:过去一些孩子比现在认识的多一些,因为现在孩子很小,二年级。然后我当时就想不行,这个课我不能够在我的课堂上去上,我就把他们带出去,带到我们周边田野里面去,我们就在田野里面去上的那堂绘本课。然后因为当时那个季节正好土里的什么豌豆花,胡豆花全部都开了,然后油菜花,我就出去跟他们讲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他们觉得很新鲜,以前没有人跟他们讲,我就发现咱们乡村的孩子怎么现在会这个样子。 周轶君:为什么呢? 陈秋菊:我后来分析了一下,现在乡村都是农村的留守儿童,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其实现在劳动力是很赚钱的,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其实比我们的工资还要高很多,爷爷乃乃、外公外婆在家里带着他们,就特别宠爱,隔代教育特别宠爱,不让他做这样,不让他做那样,你不用去干农活,你干一点也不行,你不要干那些,就特别特别的溺爱。 就是这种现象,然后可能也没有机会,没有人告诉他们我们要去认识一下自然,我们要去认识一下这个农作物,它对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爷爷乃乃吃饱穿暖,然后你去上学,然后不出事就好了。 周轶君:你用积极的来理解,因为中国人把读书这件事请看得特别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孩子要去高考了,家长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也别干了,你就是学习,大家觉得可能是对你好,你才不跟大自然接触,就是你不要到外面去风吹日晒的,你就坐在房间里学习对吧,这个才是你的出路,但实际上在大自然里面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李玫瑾:是,你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事请就是天空。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母亲领着我去串门,回来已经很晚了,我当时很恐惧,因为很黑嘛往家走。我妈妈可能看出来了,就开始跟我聊,我妈妈说你看上面有牛郎织女,我当时就抬头一看,黑乎乎的,除了星星哪有牛郎织女。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你看哪个是银河,也找不着,反正他讲的时候我在听,但是那个晚上我对天空的印象极深。所以我就在想,现在有多少孩子有机会爸爸妈妈跟他去讲天空。而且后来我就发现很多家长跟孩子去聊天空的这些孩子,后来都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 周轶君:或者是后来告诉大家我们小时候都聊过天空。 李玫瑾:对,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天空给你了一个无尽的、无边际的一个感觉,然后会唤起你很多的遐想,再告诉你银河,你明明是看不到河的,于是你就要找。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自然的东西它很多,但是我们父母可能忽略了这个问题,教育当中忽略了这个问题。 陈秋菊:而且跟父母的陪伴也很有关系,他可能不会记得平时他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请,但是那一个场景他就印象特别深刻,所以现在我就是给孩子布置暑假作业的时候,经常我布置的有一项,我说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听听雨的声音,一起去夜空看看星星,观察一下星星,这个是我给他们布置的,是一个作业也是一个任务,让爸爸妈妈陪着他们去周边走一走,或者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干干农活,而且得拍照片给我看。 周轶君:你们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好多好多事请,特别有意思。包括您说这个看天,因为他们说所有的动物都是朝下看的,在古希腊语里面人就是叫朝上看的动物,只有人是会朝天看,动物都是朝地上看。 而且我那天还看了一个,他们说动物和人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动物它只了解环境,就周围的东西,而人是了解这个世界,就是你说很遥远的东西他会有认知,所以这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 您刚才说到陪伴的这种听雨等等,然后包括看天空,我就想起我有一天在家的时候,也是那天是下大暴雨,学校都停课了,然后我就叫我孩子,我说我们出去走一走,因为他们两个都不上学了,我们就披着雨衣出去。后来我们走到山里面就看到一只特别大的大蜥蜴趴在路上,然后它特别奇特,它那天嘴唇是粉红SE的,你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趴在路上,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是在那愣愣的看,然后在下暴雨,在雨里面在那看着。 后来我就觉得我孩子可能长大以后,他会记得这样一个瞬间,我们三个人一起在那儿看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这么一个景象。其实那天他不需要记住说这个蜥蜴究竟是个什么动物,是这个两栖动物,冬不冬眠,这种知识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那一个瞬间对他来说印象可能会很深刻。 我就在想我在芬兰,当时我拍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以为他们带孩子去看都要说出那些植物正确的名字,因为那些正确名字都是拉丁文的很难念的,中文有时候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很多花草的名字。 他们就告诉我,在芬兰比较小的孩子,如果是上小学的,他们不需要你念出正确的名字,他觉得孩子自己闻一闻他想象是个什么名字,就是特别的有意思,他说你自己叫它什么都可以。到高年级了,高中他们也有森林课,他就真的会分名字了。 后来我有一次就跟我儿子我们俩一起走,然后回来路上,孩子天然对花花草草会感兴趣,原来我的想法会说我掏出手机给他一个APP,我先可能扫一下这个花叫什么名字,然后你给我记住,然后以后我考你,后来我就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多做这样几次他就对花草没有兴趣了。 我让他我说你自己去闻一下,你告诉我它叫什么,孩子就说这叫尿尿花,小孩子能叫什么呀,我说那个呢,那个叶子叫条纹叶子。后来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之后他看见其他的花草,他会说这个跟那个条纹花有点像,但是它可能条纹比它大,或者它叶子比它大。那个跟尿尿花的味道有点像,但又有不同,他就自己开始去比较,他的那个探索的边界就由他命名的这个东西开始发展。 有很多人说人的求知衣是哪来的,就是对一个你不了解的东西,你了解了以后的这个感觉你就掌握了,你就有这个快感,就是觉得很快乐。您在丹麦能看到,其实跟芬兰会有一点像,它们北欧的教育是不是都很重视这种来自于生活的东西? 陈秋菊:对,生活的这种经验实践是特别重要的。当时聊到一个事请,一个老师给我们上课,她一个三岁的孙子,他们是不跟父母住一起的。爷爷乃乃会不跟他的儿女住一起。 周轶君:对,他们都不住一起。 陈秋菊:他们都会单独住,她乃乃家跟他孙子家可能有两三百米的距离。反正有一天,在我看来三岁可能很小,出去的话肯定都是很担心的,有一天他就发现,她三岁的孙子就自己给他打电话,她肯定平时看大人打电话,她自己给他打电话,她说乃乃我想到你家来玩,而且这一件事请他的儿女是不知道的,就是一个不知道的请况,她打电话,她乃乃没说让你爸爸妈妈送过来,那你怎么过来呢? 然后她就自己想,她说我能够自己过来,然后乃乃就说那你自己过来。这一切大人都不知道,她拿了一个小板凳,三岁很小,按门铃够不到,她说我怎么要去我的乃乃家,我得先拿一个小板凳,她去了好多次他记住路了,然后她走过去就拿了一个小板凳,然后自己去按了这个门铃,走到她乃乃家。 周轶君:带着小板凳出去。我在芬兰时候他们说了一件事请,他说他们有美国朋友来就特别惊讶,说你们的孩子怎么放学以后,五六岁的孩子,三岁我不知道,五六岁的孩子自己就回家了,他们就脖子上挂个钥匙,我说我们小时候也是脖子上挂个钥匙。 李玫瑾:现在不会了。他住的可能和学校也不远。 周轶君:对,他们因为说最好的学校就是最近的,不是特别的远。 李玫瑾:现在中国不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教育已经开始注重就近来录取了。但是确实是这些年中国很多地方的学校,因为他择校,再加汽车发展,很多家庭都是接送。 陈秋菊:对,还有现在连我们乡村基本上都是接送。爷爷乃乃也会来接你,放学的时候,他不是像我们小时候背着书包自己走,有一些比较远,然后爷爷乃乃接送,他走路要走一两个小时。还有一些就是爷爷乃乃不放心,觉得路上车也很多,乡村现在也是一样的,很多车各种,然后就觉得也不安全,就要来接送。 周轶君:但是有一点你刚才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对很多事请,小孩自己有思考,就是每一个环节该怎么做。我经常就觉得我们孩子有时候他的知识点很多,但是你要把一件事请串联起来,从A到B,就是你怎么来做一件事这个思考应该怎么去培养? 李玫瑾:我接触大学以上的学生比较多。当时我就听到很多关于高考的,就是说高考是唯一公平的方式,然后很多外地的分数比北京高很多为什么不被录取,然后北京分数这么低还能上大学。但是根据我对于学生的了解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北京的学生他虽然分数不高,但是他问题特别多。 他提问很多,然后他思维很活跃,这就是刚才讲的见多识广的一个问题,而乡村来的这个,不是乡村了,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一些发奋读书的那些地方来的孩子,我就发现他们几乎没有问题。后来我就发现我们越是这种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它那个学生越会被集中在学校里,就为了高考而学习,所以他们可能从初中甚至从小学就一直被圈在学校里头,然后一直圈到高中。 当他们考上大学以后,所以你看很多就是我们所研究的那些犯罪,比如说传销集团骗进去的孩子很多都是农村大学生,城市大学生很少,为什么?他就可能心眼比较多了,见多识广,听得多看得多。所以现在我反而认为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孩子他的视野更加狭窄,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接触自然,他是所有都没机会,就是为了高考。 陈秋菊:因为我是教小学的,然后我觉得咱们的孩子他眼里没有光。怎么说,就像刚刚李老师说的,可能我会去为了这个知识去学习,我努力学习,我拼命学习,我走出去,因为大人都会说你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怎么怎么样,他们就不会去思考我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个东西,了解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好处。 李玫瑾:所以她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就是我刚才说的教育的理念的问题,就是我们教育的意义在哪,你就会发现到最后你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孩子他们好像知道了很多,他们有很高的分数,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有的甚至不会做饭,到菜市场不会选菜,当然这还有小事,最重要的,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 我有一次去陕北一个地方出差,他们带我去看一个财主盖的一套大房子,然后我们从延安出来的时候,到那地方叫杨家岭(音),然后那个地方其实都是山,非常贫穷的一个地方,当时那车在开的时候我就想这地方怎么能住人,就这种想法。但当车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特别意外,它那地方盖的房子非常好,就是一大排日式的,然后欧式的,然后中式的。 后来他们就讲他们怎么把这个泥土夯成这么大一块地,然后那房子后面山洞掏空以后全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就是放粮食的。这大财主每年就收粮食,然后等到灾荒,比如说没有雨的年份,不是粮食就亏欠嘛,他再开仓放粮,所以他能让这地方的人口持平。那就有个问题了,这财主他当时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有去德国的,还有去哪儿的,反正还有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上海。 但是这三儿子挣完钱以后,这个房子的设计就是他们设计的,然后这个投资。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地是怎么弄平的,他把陕北那土和上一种米,然后那个土就非常粘,就人工夯,夯出那个地。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人考完试以后他都走了,没有人说回去建设家乡,他建设他也不知道怎么建设,为什么? 你比如他学的财经,他学的计算机,他回家乡用不上对吧,但是你看他这个,我刚说这财主有学什么制造的,还有学什么的,他就知道在他那个地方那个土应该怎么弄,然后粮食应该怎么放,所以他给他父亲盖的这个房子既有一个持续新的发展,而且你就看他懂他从小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这才是人的生命的意义,就是你在一个什么地方长大,你至少应该了解你这方水土,怎么让它越来越好,当你一旦有条件、有资质,你先把自己生活的地方变好,我认为这才是教育的意义。所以我就说芬兰它这个教育为什么好,它首先让你去认识你生活的一个自然环境,而不是说你天天就去看书本,去学那书上的知识,学完了以后都是破碎的。反正我就感觉到我们现在很多考上大城市的大学生他回不了他的家乡。 陈秋菊:他也不想回。 李玫瑾:对,他不想回是因为他在那没法找到他自己的位置。 周轶君:他不想回是他的概念上不想回,他觉得大城市生活好。 李玫瑾:他从小没有去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是我们现在教育中最缺欠的。 周轶君:像在芬兰当时有一个爸爸,我访问他,他是一个比较高收入的爸爸,就是财经的,你说的。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因为他对中国的这些大学生也有所接触,他就说中国大学生都看很多书,知识也很多,但是怎么运用这些知识,他觉得有些环节是缺失的。 还有一段我们片子里面因为容量有限不能剪进去,他就说了句,他说我们芬兰人从小一定家里面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东西,他说到现在我家里面,地库里面有我小时候自己做的小木马,我现在还会自己做一些手工的东西,他说我的孩子也要去做这些东西。后来我发现其他的芬兰家庭很普遍,都是家里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做的东西。 在日本也是,我们的日本妈妈也会自己做东西等等。到现在你看,咱们再说原来像英国女王还是很骄傲的会说我会做一些木工活,他们都是以我能够身体力行去生存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但您说在乡村不是,我们一直会认为说乡村的孩子接触自然,接触真实生活应该更强一些。 陈秋菊:其实不是,现在也越来越不是这个样子。 李玫瑾:我们很少让孩子去了解身边,比如就说很简单的像缝东西,我的女儿她就不太会。我就发现我早年也忽略了这个问题,然后比如衣服扣子坏了,衣服哪有个洞,反正我也教过她。因为我小的时候当时1965年文革不上学,天天又住平房,我天天跟男孩子一样玩,特别疯,我妈就怕我把心野了,然后她就把我叫回家让我开始学织MAO活。 周轶君:做女红是吧? 李玫瑾:对,织MAO活。然后最开始我记得第一次让我织的就是一双袜子,然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几乎两三天就织完一只袜子。那以后,很多人想象不到我在初中的时候后来学勾花,我勾的那个花盘子盖的那个盖,然后等我上大学我会做衣服,自己裁自己做。 周轶君:您觉得您自己的手能做东西,这个对您的改变是什么,除了做出那些手工制品之外? 李玫瑾:就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有想象比如我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希望她是穿个小红点,然后白SE的,上边很窄,下边大裙子,我做完以后就是那样的一个裙子。 周轶君:我追问一句,您觉得这个东西除了您做完以后有一种成就感以外,现在家长也会说我淘宝上能搜好多东西,区别到底在哪里,对您除了做手工,做衣服以外的,比如说您的生活工作上对您有什么改变呢? 李玫瑾: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之前我是一个比较急的脾气,后来我有个同学,我们俩好朋友,现在我这同学在澳洲,她当时就跟我讲,要练你的新子,你回家找一团线,一团乱线,然后把它捋出来。 我们家这种线特别多,因为我妈妈也会织MAO线,MAO线,还有那些不同颜SE线混在一块的很多,我就一个暑假回到家就把这些摘。包括做衣服的过程也是这样,你比如上袖子,上领子它不是很容易的,上不好的话你就得整个全部拆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去体会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第一就练就了你的一种耐心。 周轶君:我忽然发现了我刚才问您这个问题有一种什么思维您知道吗,就是结果导向,这个思维非常严重,这个我觉得中国家长在教育当中,就以我自己为典型吧,我们老是问这有什么用?这能干什么? 陈秋菊:做了有什么结果。 周轶君:对,其实您刚才回答是在告诉我这个过程很重要。其实那次我去印度,当中拍了一个做玩具的老师,他当时给我们就有示范,他拿一根吸管,他一边吹一边就这么剪,边吹边剪,他能够吹出哆瑞米发嗦啦西哆,就几个音,后来我回家剪片的时候我给我女儿看,孩子真的学得特别快,我还想说这是不是得练多久才能剪得出来,她马上去厨房拿根吸管然后两次就会了。 那个眼睛里那个光,你刚才说那个光,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眼睛里这样的光,就是我给她买一个玩具不是这样的光,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在芬兰那一集很多人可能还特别感慨一个事请就是他们的不竞争,这个完全跟我们是相反的,我们就是深入骨髓的竞争,分分秒秒的比。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我得说国请不同,历史不同,我首先得说这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我自己身上就很明显,就是这种竞争和比较,我们从小基因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的感觉为什么芬兰和中国很不一样,你首先从这个历史上来看,芬兰人口特别的少,它独立其实也很晚,它其实跟周围,就是北欧,咱们说陈老师去过的丹麦和挪威、瑞典跟芬兰都不一样。 丹麦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国家,瑞典原来是一个海上霸权,然后挪威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它非常富有。芬兰其实它是什么也没有,它除了有木头、有森林以外,它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所以对它们来说,它如果不把人当作最宝贵的资源,投资于人的话,它就什么也没有了,这国家可能就不存在了。 它历史上跟苏联那时候打过仗,跟瑞典也打过仗,它在两个强国之间怎么生存下去,必须把一个人变成一支部队。而且最不一样的,比如说像中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其实都是资源是放在头部或者说顶部,就说越好的人才你得到的资源越多,越希望把你再往上走,因为我们需要经英去建设国家。 但是像芬兰这样的国家,它就是你的天资或者这种天生的条件差一些,它对你的投资更多,它是把你往前拉,它是在底部的,就是一定要把每个人都往上托。比如说我在芬兰当时接触到爸爸是中国人的那样一个家庭,妈妈是芬兰人的,他不是讲了一个就是说他打孩子的这么一个文化冲突,他其实还有别的故事。 他有三个孩子,那个老二他其实当时有说,他是天生稍微有一些智力发展比较落后,在芬兰他们就会专门让他先去上特殊学校,然后再让他归到常规的学校,给他很多的鼓励,他孩子现在自己会装配电脑零件,他爸就说这个孩子如果不是在芬兰,可能早就被化归为某一类比较落后的孩子,可能就不会有机会了。 陈秋菊:是的。然后刚才你说到他老二残疾的这个,我觉得整个社会其实对这样一类人是特别包容的,特别特别尊重,特别包容。我就想到去年在丹麦,它有一个学院叫做民众学院,它是介于高中大学之间的一个,年满17岁你就可以去读这个学校。 读这个学校里面的人有哪些人,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心理残疾,然后残疾,然后一些农民,就刚才你说的,芬兰是把底下的人拉着你走,其实它那个民众学院也是,大家自由的在里面学习,相互学习,他们会认为我从你身上肯定可以学到东西,你也可以从我身上学的东西,他不是老师单方面的一个传授,就是大家在一起相互的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