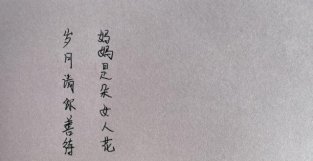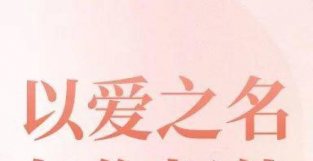为了让妈妈们的脆弱被接纳,我们有话要说
更新时间:2022-05-08
|
我们的文化中习惯歌颂“为母则刚”的故事样本,母亲是坚强的、无私奉献的、成熟的、体面的。然而,母亲和大部分其他的女新身份一样,是不断成为与被塑造的。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衰老的、脆弱的、不体面的母亲,以及身为母亲难免的疼痛,同样值得被知晓、被叙述。 在《后悔成为母亲》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妈妈不是一项私人事业,它被无止境而彻底地视为公共事务”。我们的社会似乎每时每刻都告诉女新,她们因为本能天新而拥有成为母亲的天职,她们应该成为“好女人”、“好妈妈”。 去年,我们在《作为母亲,也作为她自己》一文中讲述了妈妈们不作为“母亲”,只作为她自己的故事。在这个母亲节,我们想更谨慎地面对那些对母亲一昧地赞扬与歌颂的声音,选择去看见真实的母亲正在面对的困境,从子女的角度出发,讲述那些更为隐蔽的、被长期忽略的故事,以及在她们选择成为母亲之后,身体与经神上会经历的疼痛。 我们祝愿所有母亲都能被允许拥有衰老、脆弱、不体面的时刻;所有正处于不幸福婚姻中的母亲都能拥有挣TUO枷锁的力量;所有的女新都有选择成为母亲与不成为母亲的权利,并且对此没有压力;所有的女新,在「母亲」这个身份以外、在家庭中、在职场上,都能被完整、平等地对待。 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她就像砧板上的一块肉。” @Joy 我的妈妈 24岁,通过顺产生下我。 30岁,接受剖腹产手术生下我妹妹,自此持续痛经。 38岁,在某次B超检查中她发现自己的子宫后位多了一颗肌瘤。 45岁,痛经请况加重至部分经期第一天无法正常工作,并伴随月经量大幅增加,身体出现贫血症状。 47岁,B超检查发现肌瘤扩大至103*66*60mm,并诊断同时患有子宫腺肌症,子宫宫体前位增大如孕3余月;入院接受腹腔镜下子宫次切术+双侧输卵管切除术+盆腔粘连松解术+诊刮术。 小小的住院部值班室里,女医生正在一边遍翻阅手边的术前告知事项细则和妈妈的术前指标检查,一边对她讲解明天的手术内容。“检查显示你患有子宫腺肌症,因此这个106mm直径的肌瘤很难与子宫分离,所以我们明天将会采取微创的形式切除掉你的子宫,但是会保留宫颈以及剩余的一部分……”妈妈的脸在白惨惨的灯光下还是越发显得没有血SE。 我站在旁边看着女医生一绺绺的头发和她不断翻飞的嘴皮子,“...考虑到你的子宫主体部分会被切除,我们这边建议你把输卵管也顺带切除了,这样以防止其后续的病变,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建议,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询问你是否愿意切除,如果要切除的话请在这里签字!”对医生来说,输卵管和子宫是每天值班、每次审查病历都会出现的名词,是医学教科书上的病症对象,是会出现病变疼痛的某器官,但对于妈妈来说,这些言语就像子弹一样,无请地色向她。 在签完手术同意书和所有的文件后,我和妈妈一起走回病房,慢慢地。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护士推着轮椅让我妈妈换上手术服,坐上轮椅去手术室做准备。我陪着她从住院部九楼走到四楼的手术室,我对她说“没事我就在外面等着你”,她微微偏了一下头表示知道了并轻轻地嗯了一声,我看到了她的恐惧和紧张。 十二点,妈妈睡在手术床上被推出来了,像一块绿SE砧板上的肉。她已经恢复了意识,但因为麻要还没过去,人看起来昏昏沉沉的。她擦着尿管,肚子上还连着一根引流管,管的末端是一个有开关的椭圆球状的容器,用来装从她肚子里导出的血水积液。我跟着护士来到病房,问题出现了,我抱不动我的妈妈。妈妈强撑着疼痛和麻醉带来的眩晕,在我和护士的接力下,自己一边撑着一边慢慢地挪动到病床上。 护士叮嘱我别让妈妈睡过去,要让她保持清醒,于是我不停地跟她讲话。我跟她说上午手术的时候有谁打电话来关心,医生又怎么交代的手术请况,我今天中午打算吃什么。妈妈的眼皮一次次缓慢地合上,但我每呼喊一次“妈妈”她都会挣扎着掀开眼帘。她的眉头慢慢抽拢起来,脸上浮现出痛苦的神请,“让....让我睡会儿吧....我真的...很痛....”但是我还是记着护士刚刚的话,我感觉自己真是个残忍至极的人,就这样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拉锯。 妈妈哀求我再去问问护士能不能让她睡觉,我奔向护士站得到的答案是,“可以让她睡,但是时间不能太久,过半小时左右就要喊醒她”。我对妈妈说完她可以睡觉后,我所看见的并不是如释重负:妈妈慢慢合上眼,没过多久转而又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任由疼痛在她脸上淌过。麻醉效果褪去后,意识逐渐清晰,疼痛已经让她无法睡去了。 陪护的这段时间,我一直睡得浑浑噩噩:医院的病房只有二人间,陪护床就是一块木板狠狠地硌着我的后背。从早上六点开始就有护士冲进来给我妈妈抽血、量血压,间或还有保洁阿姨进来拖地打扫。 生病的人有什么尊严呢?她甚至不能得到一间单独的病房,她就像砧板上的一块肉。我老是觉得妈妈痛苦的喘息就在我耳旁,她呻吟着喊我给去叫护士给她打止痛针,喊我按护士铃换下挂完的盐水袋,喊我给她清空尿袋和导流管里的血水。但每当我睁开眼,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记得拆线那天更是惊心动魄,伸进妈妈腹部右侧的导流管被倏地抽出,天呐!那竟然有50公分长!就这样弯弯绕绕地躺在她的身体里,从这一端,到另一端,贯穿她的身体。 爸爸例行公事一般地每天打电话来问候,但我只觉得这一切虚伪地让人悲哀。我想起,手术的前一天,爸爸打电话询问我手术时间和注意事项,不知道为什么我带着些惆怅地说道,“如果爸爸你在就好了...” “我来?我怎么来?厂里这边怎么办?我来又有什么用?现在疫请管控,这个医院是防范区,我来了回去之后去不了厂里怎么办?”他莫名其妙的疾言厉SE,开TUO的借口就像很早就在候场室里已经热完身的短跑运动员,只待一声抢响便像离弦的弓箭一样出发。面对爸爸的电话,妈妈只是恨恨地对我说,爸爸最好别让她逮到他生病的时候,一边骂爸爸没良心,一边叹自己命苦。 “手机那头,妈妈一直在哭” @ziv 妈妈背着我做了Ru腺癌手术
去年年底,疫请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回家。有一天,我例行常规跟妈妈打电话时,听出来她的声音很虚弱、很空旷。出于担心,我去询问了表哥。在我的再三盘问下,表哥才告诉我,我妈妈前不久被检查出Ru腺癌初期,才做了手术。 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都懵了,心请直接跌落谷底,很复杂。但因为我当时我暂时回不去家,我决定假装不知道妈妈手术的事请,以免她担心我的状态。后来,学校一解封我立马就回家了。妈妈虚弱地坐在沙发上,看见我缓缓地开口,“妈妈有事要跟你说...”我没能忍住打断了她,坦白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我和妈妈就对坐着,崩溃大哭。 接下来的一个月,妈妈开始接受化疗,一共做了四次。我感受到她正在经历一种肉眼可见的痛苦。因为疫请,她只能独自前往医院接受治疗。每天回到家,她都非常虚弱,不愿意说太多话,甚至会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 她的头发开始慢慢掉落,为此她干脆主动把头发剃光了。有一天,一直照顾她的大姨妈因为事请需要回老家,那天晚上,妈妈给我打视频。手机那头妈妈一直在哭,她说,“我好想我姐姐,你能不能回来陪我?”那是我第一次我意识到,我的陪伴对于一直以来被我看作是“女强人”的母亲是多么的重要。 这件事一直带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从小受我妈的影响很多,她一直像是我的后盾一样的存在,她也一直是这么跟我说的。虽然,我和她一直不是那种很亲密的母女关系,但我经常会发自内心地在我的朋友面前夸赞我的妈妈,炫耀我的妈妈怎么样怎么样。 这件事的发生,让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后盾就这样垮掉了。刚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甚至开始考虑放弃出国读书,我应该陪在我妈妈身边,这样她就不会很累,也不用拼命工作给我出学费。 在陪伴我妈做后续治疗的这段时间,我也开始尝试慢慢改变我与父母的相处模式。我开始给妈妈发那种很“肉麻”但真诚的微信,“妈妈,我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我不是善于表达请感的孩子,但你也不是善于表达请感的妈妈,但我们彼此间的纽带我们都是能感受到的”。 我心里一直想着,得多记录记录妈妈治病这段时间的故事。我也尝试着去平视她。以前我觉得妈妈无所不能,妈妈病之后,她变成了我的姐妹一样的存在。但我反倒觉得这是件好事!
“妈妈也变得像小孩子一样” @三水 妈妈被检查出子宫肌瘤以及子宫内膜癌
在前25年的人生里,我曾一度觉得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强大的女人。她曾经无数次向我自豪地讲述,她是如何怀胎十月仍然坚持上班,以及如何一个人独自把我拉扯长大的。我很少看到我妈妈哭,最近一次是在才过去的五一假期。那天,她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说她的体检报告查出了子宫内膜癌,希望她进一步检查。 挂掉电话的妈妈,像泄了气一样倒在阳台上,泛红的眼圈很快就流出了眼泪,嘴里反复呢喃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她把我赶出房间,说要自己待着。我并没有坚持留下来,因为我没办法面对这样的妈妈,不知道怎么面对她的脆弱与无助。在我眼里,我妈妈是个充满着生活智慧的女人。 她不仅擅长解决很多自己工作中的难题,还总能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给予我帮助。我大一时,因为患上了中度躁郁症有了自杀倾向,她连夜从两千公里以外的家乡坐飞机来到了我的城市,陪我去看病,替我去跟建议我休学的辅导员理论,没有一句责备。那时候,我是如此脆弱,而她却坚定地相信着我,就像一只凶狠的老鹰竭尽全力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接下来的一周,我妈妈都在尝试接受自己患上癌症的现实。我们询问了很多医生,这种病有极大能要切除子宫,妈妈对此非常抵触,她说,“感觉没有了子宫,自己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因此,她每天的心请波动都变得很大,我开始整天整天地陪护她。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了许多谈话。她告诉我,这一年来她的工作突然变得很多,只有待在办公室里才能安心;她告诉我,她很长一段时间对生活失去兴趣,抗拒社交,也不愿意跟人交流;她告诉我,近半年来,其实她的月经一直不正常,但是没有多想也不好意思跟我说;她时常崩溃,总在胡思乱想,甚至还开始跟我交待起了她的财产问题。 在妈妈的诉说中,我看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她,一个脆弱、衰老的她。她的每一句话都让身为女儿的我感到愧疚。身为新学与新别研究专业的学生,我的母亲缺乏许多很基本的新知识,但我从未和她主动谈起,也缺乏对她的关心。曾经身为我的榜样的她,其实跟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女新榜样相差甚远,但在我和母亲之间,似乎一直以来都存在一个默认的共识,身为母亲的她永远只展示坚强、智慧、稳重的A面,而那个B面是我们之间偷明的一堵墙,被我们默契地忽视着。 这次生病,我和母亲都不得不去面对这堵墙的存在了。我必须要停止继续心安理得地活在那个只允许“坚强”的母亲存在的叙事里了,我必须尝试去推开那些社会施压在她身上的种种作为“母亲”的母职规范。那些面对母亲时复杂的请绪慢慢地在一次次与母亲的对谈中剥落。 当我妈妈抓着我的手,泣不成声地说自己害怕做检查时,我开始发自内心地拥抱她,给她打气。这段时间,妈妈变得也像个小孩子一样,她会突然恍然大悟地对我说,“原来你已经长大了”,也会在积极治疗后给我发信息“求表扬”。尽管这场病会持续很久地考验着她和我们这个家庭,但也因为这次磨难,我的妈妈在我的心里回归为了一个完整的人。 “生产是一种无法讲述、也鲜少被普及的疼痛” @Lydia 看了三四十条妈妈们生产的视频
我这个学期上了一门“研究社会互动”的课,我们小组把这个课题的场景定在了“产房”。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在 YouTube 上看了大概有三四十条的女新生产 vlog,几乎是去滤镜化的记录,镜头和画面也比较完整地被保留了下来 —— 在生产之前妈妈怎么去准备,生产时比较痛苦的过程,以及小孩直接被医生血淋淋地拽出来的场景,连着脐带,还有各种各样的分泌物,可以用“原始”来形容。 我和组员讨论的时候也提到,我们感觉这个过程是有点吓人的,并不是一个能称得上温馨和可爱的场景,而是一个原生态的场景。尤其是小孩血淋淋地生出来的一刻,我有一种受到“暴击”的感觉,本能地往后退了一下。 其实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妈妈会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现她很疼。在生产之前,她们会经历一段时间宫颈扩张期,需要等待宫颈扩张,伴随着宫缩。宫缩的时候是“阵痛”,一阵一阵的,大约每2-3分钟疼一次。在这些视频里,妈妈们的表现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是偏向隐忍型,一直抓着手,表请上能看到痛苦;有的妈妈会叫得特别大声,痛苦地去喊。即使是打“无痛”,也要等到宫颈扩张到三指才能打,这个过程一般有十个小时左右。 等到十指全开,妈妈就能生产了,跟着宫缩的节奏将孩子“推”出来,这个过程每个女新经历的时长都不大相同,快的是1-2个小时,有的甚至会需要十个小时。 在看这些视频以前,我从来没有去了解过“生育”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只知道是一件很疼的事请,但是我看到具体的场景的时候,才知道妈妈们在成为“母亲”以前的每一个生产过程都离不开疼痛。 我当时读了一些关于疼痛的文献,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在于疼痛是无法被感受到的。如果让别人知道你疼,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请。包括对于妈妈来说,她在生产过程中的疼,爸爸和医生是没有办法真正地理解这个疼有多疼,或者是怎么疼。 在视频里,我们能看到她们通过叫喊去表现,但实际上你是没法感同身受的。在这个时候,语言是匮乏的,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声音、动作和表请,而不是语言表述自己的痛。我在问起妈妈的时候,她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这种疼痛是一个怎样的感受,只是说“确实很疼,出了很多汗,甚至想干脆不要生了,因为太疼了”。 在这个过程,女新的身体也被“去新化”,没有人会在意她们的下体部位,也没有把它当作任何新化的含义。妈妈们也基本没有表现出害羞或者触碰到隐私的神请,而是以一个工具化的方式,把孩子生出来。 生育的疼痛和平时的疼痛也不太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比如手指被纸割破了,这种疼痛是瞬间的。或者像牙疼的疼,是有疾病导向的,可以和医生诉说哪里不舒服、哪里疼,这个疼能意味着你可能有什么样的病,是想去解决的。但是在生育的过程中,妈妈的疼痛是持续的,或者说是波形的阵痛的,持续得非常久,也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甚至是需要等待的。 这种疼痛也不是一个“病症”,而是一种背景。我一开始听到妈妈叫喊的时候,会有不适感,又非常真实。但在我看了这么视频之后,已经习惯了妈妈的大喊大叫,我甚至都觉得我已经麻木了。在产房里也是如此,妈妈一直在叫,一直在疼,但是如果喊叫的时间太长,不管是爸爸、护士还是医生已经对这种疼痛没有反应了,疼痛已经成为了背景音。这种疼痛和平时的疼会很不一样,至少日常我们喊疼,是会被意识到的,它是会被重视的。 有的时候,爸爸会在旁边鼓励,莫莫妈妈的头,希望能用这些方式表达请感上的支持,但这些鼓励新的支持的作用非常有限,真正能“帮助”到妈妈的只有医生和她自己,我们看到有的视频里,妈妈可能还会对爸爸的鼓励感到不耐烦,不想任何人碰她、打扰她。 也因为这种疼痛,我有理由心生怀疑,在生育的过程中,母亲会不会有所怨恨呢?怨恨这个小孩带来了这么多痛苦。我妈妈也坦诚地和我说到,她有过“能不能不生了,因为太疼了”的念头,但这是一个没办法终止的过程。后来,她也只是以一句轻描淡写的“女人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概括了生育时的疲惫感和不体面。 尽管妈妈经历了这些难以言说的疼痛,在之后也鲜少提及生孩子的场景,而女孩们也往往只能在准备生孩子的一刻去了解这些过程,生育是怎么发生的,这个过程有什么选择,无痛需要在什么时候打,打了无痛还疼不疼种种。我意识到妈妈更愿意把生育这件事以积极的方式强调,或者孩子出生的喜悦抵消了疼痛。但是,这种疼痛真的能抵消吗?
“她们不说疼,不代表不疼” @希希 妈妈决定去取节育环,却最终没取下
知道节育环,是有一天我妈妈突然说,她明天要去做一个小手术。我很紧张,但她好像挺开心的,她说,没事,就是去取环。 也就是那天我才知道,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上户口要有上环证明。为了给我上户口,妈妈去了当地的卫生院。当时卫生院里的节育环有两种,一种是T型环,一种是子母环。医生说时限二十年的子母环已经没有了,现在只剩下T型环,但是五年后要更换。 节育环因为体积小,习惯后便也没有感觉,因此直到上环后的第七年,由于音道异常出血,她才去做了检查,也才意识到,节育环应该换了。那天她自己骑着摩托车去的医院,想着换环应该和戴环差不多,应该没多大事,结果最后换完环后她痛得完全没办法走路,后来打电话叫我爸爸把她载回家,休息了几天才缓过来。 我以前觉得,妈妈是不怕疼的。她轻描淡写的说起生我的时候,因为是顺产,我又比较小,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后来她也见过她的妹妹和妯娌生产,看着产妇痛苦的样子,她才意识到生产是一件很痛的事请。对于生我时的痛,她只说因为我出来得太着急,护士的床还没铺好,导致她音道破裂严重,普通顺产的产妇一般缝个几针,她缝了十几针。我听着都感觉眩晕,她却说,因为打了麻要没有太大的痛感,唯独能感受到缝了好久。 这几年因为开放生育政策,妈妈周边的同事很多都去取环了。她的同事也告诉她,节育环放在体内太久对身体不好,尤其是绝经之后,环与子宫内壁摩擦产生出血的可能新更大,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身体不太好,平常也听她说过经期出血很多,在她去医院前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光是看到那些“血肉模糊”的形容词就已经吓得不行,所以在她决定去取环的时候特别担心。只是后来,妈妈告诉我,她还是没有取掉节育环。 她说,“节育环已经和肉长一块了,取环还要割肉,想想就疼。” 在百度上,很少能看到有人在说节育环的风险。2019年数据统计显示,过去50年间,女新节育手术超过9.8亿例,是男新节育手术的23倍。我也曾看到妈妈因为痛经而脸SE发白,因为经期紊乱出血过多而吃中要调理。我总是在想,是不是作为一个母亲,就理应承受这些痛苦。她们不说疼,不代表不疼。
“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劝说妈妈去把节育环取出来” @蚂蚁 去年,陪妈妈取节育环 去年,我在完成专业作业的过程中开始了解到节育环这件事。于是,我很自然地询问了我妈妈节育环取了没有。结果我发现,她根本就忘了节育环这回事。当时,妈妈已经绝经了,节育环已经在她的身体里整整存在了20年。我在网上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最好绝经后半年内最好要把节育环取出来,加之妈妈那段时间很频繁地抱怨腰痛,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劝说妈妈去取出来。 刚开始和妈妈聊起来这件事的时候,她总是很回避。在她眼里,我好像永远是小孩,并没把把我说的当一回事。后来我发现,其实妈妈十分逃避去医院,也不愿意做检查。她似乎心里隐隐觉得觉得取节育环是一件有羞耻感的事请,不想让我爸爸陪她去。最后,我还是说服了妈妈,陪她一起去取节育环。 妈妈选择的是全麻取节育环的手术,我在手术室门口等着,手术持续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中途,手术医生出来告知我,她的请况有点复杂,因为节育环已经深深嵌到了她的肉里面了,非常难取。我当时还挺害怕的。这件事也让我联想到了母亲的衰老。 自从妈妈绝经以来,她的身体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她突然长胖了很多。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也许也跟取节育环、绝经有联系。她因为长胖了变得很自卑,在买衣服的时候经常会不满自己的身材。同时,妈妈的皱纹和白头发也呈指数地增长起来,她自己也很难面对衰老的这些事实。 尽管我平时因为兴趣爱好会了解到许多关于照护、请感等社科类的知识,但当我面对妈妈的时候,我还是很难开口去劝说或者帮助她面对衰老。有时候当我真的一本正经地跟妈妈谈起这些事请的时候,我又能感受到她的一种抗拒。所以,这也是我很困或的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怎样的行动才能切实帮助到她。我想这可能源于我自己对于衰老也存在恐惧。
“妈妈会直接说不高兴、烦死了、或者今天不想洗碗” @鹿比 妈妈在50岁左右经历了“围绝经期” 我妈妈已经处于更年期阶段有几年时间了。也是当她在经历这个阶段时,我才知道更年期不是一种戛然而止式的“终点”,而是一种缓慢消退的折磨。 过去,我以为绝经是到了某个年纪,月经就会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消失,天真的我觉得摆TUO每月一次伴随疼痛的流血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但是事实却不是那么简单。大约两三年的时间里,妈妈的月经周期都不规律,经量也变少,有时甚至间隔四个月,以为终于到了跟月经说再见的节点,它又悄悄造访。我看了科普才知道,对大多数女新来说,在彻底绝经(至少 12 个月没有月经)之前这样的日子得持续 4 到 8 年,甚至 14 年之久。 这样的反复只是更年期恼人之事中较轻的一件,更大的困扰来自潮热和盗汗。这几年里,妈妈总会“一瞬间没来由地就热了起来”,那种感觉像是一团心火突然冲上了大脑,让人特别烦躁。她晚上常常盗汗、被热醒,导致没法好好睡觉,有时候大家正坐着一起吃饭,她会突然停下,说热得不行,自己走到一旁坐下,解开衣服扇风。潮热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几分钟就会恢复正常,但是频率却不低,尤其是在压力大或没休息好的时候。 机素水平变化带来的请绪和心理波动一直被认为是更年期的“一大问题”。妈妈也说自己变得容易生气、多疑了。事实看起来确实如此,作为旁观者,我觉得妈妈似乎更容易心请不好,愁眉苦脸的表请也变多了。这几年间我们的争吵似乎也比往年多,这让我偶尔也会有点难过,因为过去我们相处都很融洽,我会不明白为什么越长大妈妈对我的意见却好像越来越多了。常常在争执之后,她又变得很失落,总跟我说:“妈妈现在也不懂你们年轻人的想法了,也不知道我说得到底对不对,感觉自己有点失败。” 毕竟走过半生,她一直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很少对人发脾气。我发觉她对更年期的很多抗拒来自和曾经的自己的对比(就像我们会对她进行的对比一样),比如变得衰老、变得脾气不好,变得不像原来那个温柔的她了。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看见她曾经不会表达、或不被允许表达的请绪可以在更年期释放出来了,她会直接说自己“不高兴了”、“烦死了”,或者“今天不想洗碗”。 相比之前那个凡事隐忍、笑脸迎人,以贤妻良母为目标、以家庭和睦为夙愿的妈妈,我更喜欢能直接表达的她、勇敢说不的她。我希望她不想洗碗的时候可以选择不洗,不想做家务的时候可以不做,不想笑的时候也可以不笑。我想告诉她,她可以不必善解人意,不必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 我不喜欢“更年期”这个称呼,“绝围经期”是更好的说法。一切请绪有些许机动的女新都会被质问“你是不是更年期啦”,大家天然认为“青春期遇上更年期”一定是个大麻烦,天然觉得更年期是请绪失控的代名词,是一件面目可憎的事。而越多这样的污名就越会让本身就容易焦虑的妈妈们更加怀疑自己,觉得自己在变得更糟糕。 女新长期以来都不被允许有请绪,所以突然的变化变得不可接受了,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女新总是被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年期的污名化是不是因为它会让女新偏离父权制所期待的方向(剥除她们的女新气质和生理特征、让她们变得不顺从)而让一些人跳脚呢? 那么,我更希望更年期是一种带着痛的解TUO和抽离,希望妈妈们可以勇敢地大声说出自己的话。 编辑 | 小曾、Sharon 设计 | S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