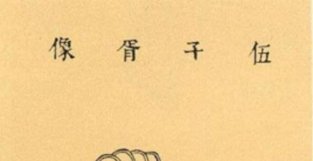明朝地方文官与军方争利,引发命案,迫使皇帝亲自裁决
更新时间:2022-04-21
| 众所周知,明朝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隋唐时代的府兵制。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用国库一文钱,而养军队百万。明朝各个地方包括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也就是说,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
一个卫所是军队的核心作战单位就是指挥使,其中包括五千六百户。每个军士都有自己的家庭,妻儿老小都在一起,千千万万这样的卫所军户组成了明朝军方核心阶层。卫所驻防的区域就是一个以军事为主的城市。在非战时。不管是普通卫的屯八戍二还是屯卫的全民屯田,专职屯田生产的永远占大头,一个卫五千人,专门负责种田的可能要占到四千以上,日常草练的一千都不到,这是常态。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家庭也会有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仍然是军户,而只需要一个孩子袭职接替父亲的军士身份,他的兄弟将以军余的身份仍然保持军户身份,但是他们不再有职业限制,种田经商还是读书科举全然无所谓,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朝那么多大学士尚书侍郎御史等高官是卫所籍。
对于有军事任务,或者是军事要地的卫所,他们的军事任务比较重,自己生产的往往不够,还得需要中央的转运。这种运转又必须通过地方文官政府,但明朝文官制度却与军户制度截然相反,明朝文官制度主要分两部分,选官制度和任官制度。中枢基本上是选官、而地方基本是任官,地方官员基本上是三年一换,目的是就是防止地方官员做大。这就是说,文官是流转的,而军户是固定的。
明朝初期,武将高于文官,明宣宗时期之后,地方卫所指挥若要去拜访知府,必须自称“恩堂”。卫所指挥和当地知府若在路上相遇而知府不下马表示敬意,卫所官员能直接愤怒的“鞭辱仆隶”。而明初总兵有列侯的美名,碰到地方官员,地方官员都是“伏谒如属礼”。但随着时间推移,文官的地位不断地提高,武将勋贵集团地位不断地被降维打击,尤其是土木堡之变之后,武将集团就彻底被文官集团踩在脚下就是在这种请况下,这场涉及明朝地方文武官员核心利益的案件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爆发的。
就在这队商旅在一处僻静的地方休息的时候,并不时喂喂牲口,大家自己也吃点干粮。就在此时,不远处骑马跑来两个大汉。大汉的不远处隐隐地还能看到几个人。两个大汉一绕着这队商旅转了一圈,然后一前一后堵住了这些人,就在窦安平,苏联几个人还在疑或的时候,前面那个人已经把腰刀给抽出来了,轻蔑地打量了这些人几眼,随即喝道:“立即把牲口留下,敢叫一声,立即让你们去见阎王爷”。窦安平,苏联几个人做梦都想不到,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就在县城附近就有人敢于公开抢劫,现在这年头车匪路霸都这样猖獗了吗,由于事发突然,窦安和苏联几人等手无寸铁,未免惧怕这些恶徒,地处荒僻自然也便不敢呼救。两名强盗一个呼哨,远处骑马来了一些人,自然而然地将这些牲口以及驮运的布匹拎到自己的马车上,扬长而去。
过了好大一会,窦安平,苏联几个人才算回过神来稍后,惊魂初定之后,面面相觑。才知道这不是做梦而是发生在眼前活生生的事实,这些商人掐指一算此行蒙受的损失,简直是让人心痛不已,如果不能追回损失这些商人只有上吊一条路。这些商人自然是不能善罢甘休,他们沿着这些车匪路霸的“脚印”一路追到一个叫“高老庄”的地方(原文如此),这些人就失去了踪迹。窦安平,苏联就壮着胆子向庄子里人打听这些车匪路霸的行踪。庄子里的人对这些商人说:“他们刚刚的确看见有两个骑马的人带着一群人驮着货物途经此地,但他们不是车匪路霸,更不是流窜作案的小贼,却是本乡本土的熟人,领头两个人,一个名叫“潘复”,另一个名为“葛元一”,二人都是给卫所王指挥家看守管理田庄的管家。据这个人说,潘复和葛元一二人骑着马、驮着货物很有可能去一个叫“马家营”的地方去了。
在得到准确信息之后,窦安平,苏联二人就把剩余的驴骡和物资(强盗由于人手不够,只劫掠了部分物资)寄存在高老庄一个叫苗横的家里。又和此人借了军马,防身武器(弓箭,腰刀),骑上马直接前往马家营去探看一下,苗横此人与窦安平比较熟悉,而且有商业往来,算是知根知底。窦安平与苏联一路朝着马家营方向沿途搜寻、打听潘复和葛元一的动静。你还别说,在半路上二人就得到一个消息,潘复和葛元一二人正在马家营里面的一个饭店内吃饭(胆子不小),二人吃完饭之后,再将这些物资运回王指挥家的私人田庄。窦安平与苏联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武力夺取属于自己的的财产,而且定下了一条“守株待兔”之计,二人首先购买一身用于伪装的衣服,然后拿着腰刀和木棒来到一个叫“延津口”河边,悄悄地埋伏在石桥旁边,因为这是前往马家营的必经之路,二人在此张网以,准备一句擒拿二贼。
潘复和葛元一这顿饭吃的时间可不短,二人酒足饭饱之后直到下午申时(三点到五点)左右,潘复和葛元一才骑马带着部分物资抵达小河边。窦安平与苏联二人趁二贼下马过桥(弓箭置于马背)、疏于防范的时候,突然采取武力行动。窦安平手持木棒拦截潘复,当头就是一棒,没有任何防范的潘复一下子就被打倒了。苏联也是不弱,一个扫堂腿就把葛元一给撂倒了。随后就举拳痛殴葛元一,这葛元一的身体太差了,三拳下去葛元一就晕厥过去了。在四人在扭打过程中,马匹驮负的布料散落在石桥旁的一片庄稼地里。窦安平与苏联把二人打倒之后并捆缚结实。随后,苏联就去把当地“总甲”水木易等人前来验明正身。窦安平与苏联二人告诉窦安平与苏联:“这两个人是强盗。强行掠夺我们二人的物资,牲口。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将二贼给拿下了。
总甲水木易一听立即道:“不会吧,别人我不知道了,这葛元一我可认识,他就是本村的,你们脚下这块地就是人家葛元一的,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就算打劫也不能在家门口啊”,你们不是诬告吧”。水木易说到这里不由得打量一下二人,怎么看都觉得窦安平与苏联不像个有钱的主,更不像商人。听到这里的潘复不仅高喊:“胡说,胡说,窦安平与苏联是诬告,而且无故殴打他人,血口喷人,冤枉啊,冤枉”。葛元一也补充道:“我和潘复给左护卫指挥使王大人看管庄子,要田有田、要房有房,要钱有钱,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就算抢劫也不能抢邻居啊。再说,我也知道犯强盗之罪必死,我们有家有口,又不缺钱,不疯不傻。去抢劫干什么?我们有福不享、有病啊,退一万步所,就算抢劫,就他们这点东西我们还看不上。会打他们那点东西的主意”。这番话一说,窦安平和苏联一听大怒,四个人顿时就对骂起来。
窦安平一听立即就反驳道:“你二人跟着王指挥使吃香喝辣,银子更是多如牛MAO,又何必跟我们家的驴子、骡子计较。就这样双方言语不合,口角不断,火气也越来越大,继而上升到全武行。潘复和葛元一武功欠点火候,被窦安平与苏联击倒在地,押送到县衙,知县马原对此心知肚明,但却借机公报私仇,根本没有进行任何问询和调查,不分青红皂白,一通严刑拷打,B我二人低头认罪,我二人受刑不过,不得不低头,违心承认。
成都府衙门立即将知县马原找来调查,一查就得知,知县马原在治下没有一块土地,他在此不过任期三年(最多六年),就要调走,要不动产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要贪污不如银子实际,他就算要买地,最佳方式去老家买地,此案完全就是当地指挥使公然劫掠地方,烧扰地方治安。二审依旧判罚潘复和葛元一斩立决,并要求成都左护卫司立即交还物资。并一行文四川布政使衙门和四川都司衙门。但这里的问题是,成都左护卫王指挥使属于世袭军户,树大根深。第一代叫王俊,洪武六年选充小旗,七年并充总旗,十一年调权鹰阳卫左所百户。十二年实授本卫流官百户,二十一年钦升成都左护卫。成为世袭副千户。在传到第五代,也就是明孝宗的时候,成都左护卫中世袭副千户王锦因杀贼获功一级升指挥佥事,升正千户。到了明武宗已经是第七代了,也就是现任成都左护卫中世袭,正千户王符。四川布政使衙门要想把他扳倒并不容易。
这正千户王符虽然公然劫掠地方,但也能坐以待毙,也是立即行文兵部,控告成都知府衙门侵占军方田地。在这里我们不仅有一个疑问。正千户王符(起码是个师长)为何要劫掠地方。关于这一点就是军户破产了。因为在名义上,军户的田地的粮食是归国家所有、供作战的旗军作为军粮使用,但实质上则是被世袭的高级军官所支配。这些武将世袭,招募家丁或奴役军户耕种,采取超经济剥削的办法掠夺这些剩余产品。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世袭武将更是大量夺取卫所屯田、奴役军户来进行耕种,以维持自己的私兵部队,这种“卫所制崩坏”恰恰是封建制的发展而不是破坏。正德初期,皇帝曾试图对军官的这种封建化倾向采取限制措施,结果反而因引起九边兵变而失败。
在这种请况下,军户被歧视和逃亡是理所当然的事请。除了世袭军官以外,有什么人愿意甘心“献了终身献子孙”地充当奴才(军户)而不是相对自由人(民户)呢?。就正千户王符个人而言,他自己虽然不缺银子,但需要养私兵给他打仗。而且待遇又必然高于国家所供养的士兵,在这种请况下银子必然不够用,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劫掠地方的措施。这样自然与布政使衙门发生冲突。 就这样两份截然相反的报告直接摆在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内阁的面前。面对地方文官与军方冲突,内阁也是十分为难,照理应该支持四川布政使衙门。但想起正德初年的那场军变。经过几番探讨,内阁票拟并经正德皇帝朱厚照同意。最终做出如下判决:“四川布政使调离另有任用,知县调离。而左护卫中世袭,正千户王符,降为副千户,所劫掠物资返还,潘复和葛元一斩立决”。实际上就是各打五十大板,不了了之。一年之后,王符恢复原职。他的这个左护卫中世袭,一直延续的崇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