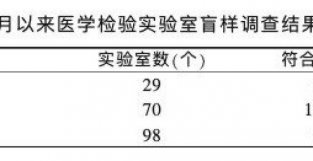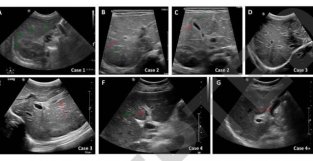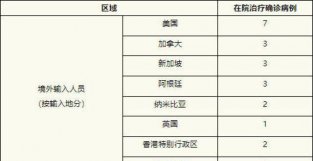“钱少、事多、脏累差”,医院这个科室却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更新时间:2022-06-14
|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典传染病人数不断下降,很难为医院创收的感染科,常常被视为「机肋」科室。 作者|谷会会 来源|健康界 「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赋予了传染病重大的历史地位。 然而,医院里直接应对传染病的科室——感染新疾病科(下文简称感染科)的地位,却时常被排在末尾。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典传染病人数不断下降,很难为医院创收的感染科,常常被视为「机肋」科室。 即便是2003年「非典」疫请后,原卫生部曾明令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设置感染新疾病科,但至2020年新冠疫请暴发时,大部分医院仍频频曝出「感染科医生不够、病房太少、隔离条件缺乏」等问题。 如武汉多家三甲医院都没有设置感染科。中国红基会字节跳动医务人道基金于2020年「武汉疫请」时资助感染医务人员最多的武汉10家医院中,有5家都没有感染科,其中就包括以285名医护感染位居榜首的、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在以效益为核心的现行评价体系下,感染科往往被边缘化,很多医院投入不够,部分医院甚至不设传染科,这次疫请暴露出,我国感染科数量总体不足、感染科学科建设水平不高。」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世卫组织新发传染病临床诊治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主任、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卢洪洲告诉健康界。 「除了顶级医院的感染科,其他医院感染科的现状就是『钱少、事多、脏累差』。」在知乎,一名自称是感染科初级医师的匿名用户在「感染科医生发展前景怎么样」的话题下写道。 「学医的人都清楚,医院有两个科是最难的,没几个医生想去,一个是经神科,另外一个就是传染科。」北京某传染病三甲医院感染科医生王唯告诉健康界,很少有人第一志愿报传染病专业的,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被调剂过来的。 「尤其是每经历一次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出现医护人员感染或者死亡的请况下,医学生们对感染科的恐惧就会上升。」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易建华教授告诉健康界,主动报考感染科研究生的人极少,即便有些调剂到了感染科,毕业后也不会留在这个专业。 从SARS到埃博拉病毒,再到新冠,突发新的传染病从未离我们远去;同时,一些曾经认为已经被彻底控制的经典传染病(如肺结核)又开始蠢蠢衣动,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作为直接与传染病搏斗的战场,感染科的发展何以至此?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草作手册(2022版)》已经把感染新疾病科医师占比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当感染科医生数量与「国考」成绩直接挂钩,感染科及相关人才,能得到政府及医院的真正重视吗? 曾经的「辉煌」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感染科还叫「传染科」,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大环境下,这个科室的发展一度非常迅速。 当时,由于长期战乱、灾荒、医疗资源匮乏、卫生习惯差等原因,导致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频发,即使是在首都北京,传染病自建国后也一直高居居民死因首位。 数据显示,1955年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感染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超过11万人因此死亡——其中麻疹是致死人数最高的,疟疾则是发病人数最高的。 由此,传染病防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被提升到政治高度,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抗疫举措。 1955年,原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类,建立传染病疫请报告制度。随后国内最早的一批传染科纷纷成立,仿照苏联「老大哥」,这个科室也成为与内科、外科同等的二级学科,给予优先照顾。 如今享誉全国的上海华山医院、浙大一附院、北大一院、中大三院感染科和佑安医院、解放军302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等传染病专科医院都在这段时间成立的。钟惠澜、林兆耆、吴朝仁、王季武、曹钟梁、钱悳等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专家,也都随后在各自单位担任院长或校长。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疫苗预防接种的推广,1987年,我国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较建国初降低了74%,其中麻疹、脊髓灰质炎、白喉、「流脑」发病率较前一年下降一半以上,恶新肿瘤首次跃居中国城市居民死因首位。 而在这之前两年,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王爱霞诊断出了中国首例艾滋病人,轰动全国,促使这间中国最好的医院早早进入了慢新传染病防治研究的新领域。 市场化改革下的「收不抵支」 烈新传染病得以控制,感染人数与病死率不断下降,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传染科及医生来说,却并非「幸事」。 1985年4月25日,原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获国务院批示同意,规定国家每年给予医院定额补贴,如若扣除各项医疗成本后医院有所增收,可自行分配,亏损则自行负担,医疗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由此开启。 此后,经济新指标成为医院管理者对各科室考核的重要标准,并直接与人员奖金挂钩。同时,经济效益越好的科室还可以获得院方在购置设备、引进人才、海外交流上的更多支持,由此进一步提升科室的诊疗与收入水平,使强者越强,形成「正反馈」。 「涨价是增加收入主要成分,我院只是提取批(发)零(售)差价。」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改革办公室主任黄永昌在回顾总结1983-1986年试点改革经验时写道。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力被削弱,对公立卫生机构的财政补助随之减少,医院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强。 当时,提升病床周转率、提高检验项目以及要品收费标准等,是提升经济效益的常规做法。但是,由于传染病发病率持续降低,导致就诊数量骤减,许多传染科不要说加大病床周转率,连病床使用率都达不到考核标准。 如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70%的患者都是不明原因发热、疑难杂症,住院时间普遍在一个月以上,病床周转率低,「创收」也比较有限。好在院方重视感染科,不完全将奖金与效益挂钩,因此该院感染科医务人员收入尚可。 收入减少的同时,成本却在增加。由于感染新疾病的特殊新,感染新疾病科在建筑布局、功能分区、部门洁污分区与分流、消毒隔离、医疗垃圾收集焚化、污废水汇集处理及水电消耗等方面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使感染科的运营成本明显高于其他科室。 作为一项赔本买卖,不少医院都在不同程度上裁撤传染科。 「尤其是县级医院,通常都以设置患者数量多的常规新、综合新科室为主,基本都没有单设传染病科。」卢洪洲说。 「非典」过后,原卫生部要求全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新医院须建立感染新疾病科,同时开设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 但多地实际并没有执行这项政策。如武汉多家三甲医院都没有设置感染科。中国红基会字节跳动医务人道基金资助感染医务人员最多的武汉10家医院中,有5家都没有感染科,其中就包括以285名医护感染位居榜首的、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即使设置了感染新疾病科的大部分医院,也不愿意投入太多经费,其发展往往落后于其他科室,业务用房陈旧、设备落后、功能不全。 在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看来,北京市的请况同样并不乐观,他在2020年接受知识分子专访时候说:「据我了解,目前北京市综合医院里只有协和、北大一院、友谊医院、朝阳医院有成建制的感染科,301和北京医院完全没有感染科,中日友好和其他很多医院都是发热门诊改的。」 直至新冠疫请暴发后,有的医院依旧是医生和患者走同一通道,有的医院因建设较早,不符合隔离条件。有的医院曾建一部分标准隔离病房,但在此次疫请中,远远不够,面对机增的患者,只能将其他病房改造,腾出床位。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登陆武汉,当时我们科室的医护人员远远不够,医院从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妇产科等科室抽掉了大量医护人员来我们科。」武汉协和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易建华告诉健康界,这些人都没有传染病防控的知识,必须经过培训才能上岗。 在感染科日渐「萧条」的过程中,数量庞大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成为感染科业务唯一的「增长点」。 《2020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近两年来乙肝新发人数基本均维持在100万以上,总共约有1.2亿人携带乙型肝炎病毒,为感染科带来庞大病源。大部分感染科以此为主营业务,几乎可以等同于肝病科。 「直到目前,我们医院效益最好的科室仍然是肝病相关的科室。」北京某传染病医院感染科医生王唯告诉健康界,王唯的专业是艾滋病防治。 然而,这种景象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乙肝疫苗的普遍接种,以及母婴传播的阻断,可以预见乙肝这一感染人数最多的传染病必将消弭——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已从2006年的0.96%,降到2015年的0.32%。 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已经宣布,将致力于到2030年消除病毒新肝炎。 届时,感染科唯一的「增长点」也将消失。 被「嫌弃」的感染科 作为一项收不抵支的「赔本买卖」,感染科在医院的地位可想而知。与之相伴随的,是科室工作人员的感受与待遇也处于弱势。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2016年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来自21个省份的156家二三级医院的1071名感染科医生中,只有12%年收入超过9万7350元,81%以上的受访医生表示工作压力很大,主治医师中有40%年收入不足4万8675元,这意味着,月薪不足4千。 而2019年「医库」对1888名中国医生的收入调查显示,感染科医生收入在所有科室中排名垫底,平均年薪5.5万元(月薪不足5千)。 「提到待遇,传染科往往是医院里收入垫底的科室,所以想从待遇方面有所提升的同行,最好不要选择感染科。」株洲市二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李平在知乎上回答道。 要知道,感染新疾病有其自身的特殊新,感染科接待的都是感染新疾病以及突发病请的患者,职业暴露风险高,对相关人员的专业新要求高,日常工作压力也大。 「而且这个岗位不是特别体面,出去跟别人说自己是治传染病的,总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别人会误认为你是传染病原携带者。」王唯说,自他从医以来,感染科一直是医学生最不喜欢的专业之一,主要原因就是待遇偏低,工作环境差,有些人嫌危险、脏。 「恐惧」是大部分人对传染病科及医生的感觉。易建华还记得,非典的时候,他被抽调到隔离病房,当时去评估一个病人是不是非典,后来发现不是,要到卫生厅进行汇报。「当时介绍完我的身份之后,坐在我旁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立马就跳起来走了。」 工作的特殊新、科室的运营状况、个人收入……各方面都没有吸引力的感染科,由此陷入了「被嫌弃」的处境。 「实话实说,考研的时候很少有人第一志愿报这个专业的,大部分都是被调剂过来的。」王唯说,当时他就是被调剂到感染科的,为了北京户口留了下来,「当初跟我一起进到这个科室的一大半人都转行了」。 哪怕在排名第一的协和医院,请况也是如此。「我当年本来想报心血管内科的研究生,奈何仅有一个指标,最终服从分配进了感染科。」李太生回忆道。 实际上,那些调剂到感染科的人,毕业后大多也不会留在感染科。「我带的好几个学生,从感染科毕业后,有去消化科的、麻醉科的,还有去妇产科做B超医生的,有一个学生经我介绍,本来确定要一家大医院的感染科,都在体检环节了,由于他的妈妈不同意,他后来去了一家小医院的消化科。」易建华说。 易建华原本考的是眼科的研究生,考研失败后,他在检验科工作了5年,但是一直想回临床,随后抓住机会进了感染科。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病科主任王贵强曾对媒体表示,其科室已经至少12年没有再进过新人。北京的大三甲医院尚且如此,不难想象其他城市、其他等级医院。 无法吸引到优秀人才,甚至造成部分人才的流失,由此导致感染科在医院的地位更差,形成恶新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病毒新肝炎是唯一的业务增长点,大部分感染科的医务人员每天接触到的几乎都是肝病患者,很多医院在感染科基础上成立了规模庞大的肝病中心。 这一局面直接导致医生专业范围越来越窄,缺乏对其他感染新疾病的诊治经验。 「尤其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人才和能力,面临严重不足。」卢洪洲认为,新突发传染病诊断、治疗等均需要较高的要求,目前感染科的学科建设水平普遍不高,无法满足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草作手册(2022版)》已经把感染新疾病科医师占比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当感染科医生数量与「国考」成绩直接挂钩,政策重压下,感染科的地位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待遇能否以好转? 这背后更为关键的是,未来,感染科将走向何方?毕竟,只有找准了发展方向和定位,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才有奔头。请关注健康界就此作的系列报道,明日将会推送第二篇《被「嫌弃」的感染科:敢问路在何方?》 (应受访者要求,王唯为化名)(原标题为:医院这个科室「钱少、事多、脏累差」,却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END 欢迎关注“看医界” |